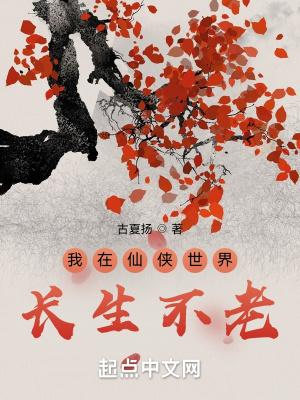UPU小说网>那个小哑巴布丁琉璃txt > 第5章(第2页)
第5章(第2页)
第二天,林知言加了护理师关倩小姐的微信,按照约定赶往山顶别墅。
见到笑眯眯在浴室等候的林知言,霍依娜将眉毛拧得能绞死人。
“你还敢来啊,贱不贱?”
她毫不留情地讥讽,双臂环胸靠在轮椅中。
那是一个典型防御的姿势,看来昨天的相处并没有完全打消霍大小姐的敌意。
昨天的事,我开始的确有一点生气,聋人没有助听器真的很不方便!但要说记恨倒也谈不上,毕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林知言将职业道德发挥到极致,见招拆招,反正再丢几副,霍先生也赔得起。
提到霍述,霍依娜的神色微妙一凝。
她扭过头,意义不明地哼了声。
“喂,你耳朵怎么坏的?”
被抱进舒服的按摩浴缸后,霍大小姐没忍住开了金口。
林知言抬头,眨了眨眼睛。
她失去听力那年,只有四岁半,因为药物中毒。
突然坠入无声世界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不仅是身体的不适,更是心理的折磨。林知言隐约记得一些模糊的画面,刚聋的自己没日没夜地嚎哭、尖叫,推搡摔打一切能触碰到的物体,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声音的存在,直到喉咙嘶哑、精疲力竭,破坏力比现在的霍依娜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直到三年后父母因车祸去世。
一切都戛然而止。她不再无意义的哭闹,或许是长大了,又或许是因为她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可以任性妄为的资本。
在某种程度上,林知言甚至有些理解霍依娜的恶劣行径。
当自身痛苦难以排解,就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折腾自己,要么折腾他人。
霍依娜从泡泡中露出一颗脑袋,听林知言“说”完,恹恹问:“这么说来你是聋子,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会说话?”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麻烦,林知言抬头想了想,打字转换语音。
我不说话的理由,大概和你不想让别人看到身体的理由一样。
因为内心过于敏感,所以不敢面对缺陷。
“搞什么,好像你很了解我似的。”
霍依娜面上嗤之以鼻,泡沫下的手掌却不自觉摸向腰椎处的扭曲凸起,大腿上的伤疤更明显,很丑,很可怕。
要换做平时被戳中心事,霍依娜早就发疯炸毛了,但小哑巴的眼睛太过于干净澄澈,整天笑吟吟没有一点阴霾,搞得她连生气都提不起劲儿。
她兴致来焉,抬手在林知言手臂上拧了一把。
好痛!
林知言刚抬头,霍依娜又在她小臂上揪了一把,像是发现什么新奇的玩具:“不是吧,这都能忍着不出声?”
“……”
林知言捉住了霍依娜的腕子,另一只手抓住泡泡堆下的浴袍,用力往下一拉。
霍依娜身体不受控制往下一滑,仓皇尖叫一声,忙伸手攥住浴缸边沿。
林知言单手敲字,很用力:霍小姐,我不是橡皮泥,很痛!你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我就把你丢浴缸里不管了,你自己想办法起来吧。
“你敢!”霍依娜呼呼喘气。
林知言挑眉:由奢入俭难,你试试看。
两人瞪眼对峙一分钟,霍依娜嘴唇一抿,彻底安分了。
……
阴云盘桓于顶,才刚过18点,天色已近全黑。
霍述进门踩着靡丽的灯影进门,随手解下外套搭在椅背,拿起一枚金字塔魔方坐在沙发上,慢悠悠转了起来。
这是他的习惯,这种低阶的魔方对他来说毫无难度,但很适合宁神。
老爷子在山城有一份产业,下午他第一次去公司,遭到了不少刁难,不用想也知道是受谁指使……
京城那位嫡子,到底坐不住了。
叮咚一声响,手机屏幕上弹出一个诡萌的小丑头像。
这是霍述另一部手机,专线加密,发来消息的只可能是国外M大研究所里的那群神经病。
霍述随意靠在椅背中,单手点开屏幕,Vincent的消息立刻跳了出来。
我和Alfio打赌,赌你回国活不过三个月。所以Shu,你死了吗?
霍述挑眉,屏幕的光在他眸底泛出幽幽的冷意。
他一手撑着额角,一手握着手机,百无聊赖打出英文回复:抱歉,让你失望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活着啊,啧,那真是太可惜了!
那边惋惜,不过我们还是不理解,你挣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干嘛还回国蹚浑水?May收集过资料,你那个便宜哥哥好像很不好对付啊!Shu,你现在的日子应该很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