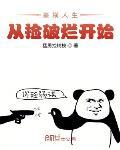UPU小说网>红糖鸡蛋酒糟的功效 > 第64章 第 64 章(第2页)
第64章 第 64 章(第2页)
梁白玉弯腰捡起蛇皮,拿在手里捏捏摸摸。
“蛇蜕皮,是成长。”梁白玉呢喃了声,手肘蹭一下陈砜,“那你知道人蜕皮是什么吗”
陈砜被问得一愣。
“人蜕了皮,就什么都不是了。”梁白玉意味不明的说完,哈哈笑道,“人也不可能蜕皮啦,说着玩的。”
陈砜凝视他苍白的脸和漆黑的眼,有些出神。
梁白玉丢掉蛇皮,把手在陈砜的褂子上擦擦“映山红还没开。”
陈砜道“快了。”
梁白玉朝一个方向歪了歪脑袋“那边有金银花,我在这都闻到香了。”
荆棘丛里生了一片白。
陈砜掰下一些再利用枝条编了个手环,套在梁白玉的腕部。
梁白玉举起那只手,眯眼看一圈白花和绿叶,他凑近闻了闻,转头对陈砜笑得比花还艳“我喜欢这个,你以后每年都要给我编。”
陈砜揉着梁白玉后脑勺的头把他摁进胸膛。
每年
没有了,今年都过不完了,也不会有明年,每年了。
我是要跟你一起走的。
另一个世界或许也会有金银花到时候再给你编花环。
陈砜无法判断梁白玉那三粒药的药效是多久,他内心的焦虑慌乱都被现实磨光了。
喂梁白玉吃下药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做好了和梁白玉迎向终点的准备。
梁白玉的精气神差不多回到了去年年底的状态,还没说话眼睛就笑了,他披着长唱京剧,改了调子,凄楚淡了,多的是涓涓细流的平静。
陈砜会什么都不做,只听梁白玉唱京剧。
而当他拿着大笤帚扫院子的时候,梁白玉就坐在院门口看他忙。
“都是灰。”陈砜道,“你回屋去。”
梁白玉摇了摇头“不要。”
陈砜只好由他去。
梁白玉懒洋洋的往后靠,竹椅前面的两条腿翘起来,重心不稳的吱呀吱呀响,随时都能倒的样子,但就是不倒。
堂屋正对着梁白玉,门是由木板拼成的,门有大大小小的缝隙,会漏光,却也挡不住风雨。
门底部黑长霉。时间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有。
梁白玉微垂的眼里泄出的光在所见之处跑了一遍,他闭了闭眼,撸一把怀里的小黑狗“财啊”
财哼哼唧唧的蹭他。
“小傻狗,认得我了吧,认得啊。”梁白玉捻它下巴上的毛,眼前浮现的是一串干瘪的山芋藤手链,和几片树叶,它们被放在抽屉的书里,是他无意间翻到的。
那是一个阅历丰富,外形硬朗内心柔软的男人朴实的浪漫。
“陈砜。”梁白玉喊。
男人停下挥动笤帚的动作向他看来,眼里都是他。
“我想听你吹口琴。”梁白玉说。
不多时,院里就响起了口琴声,吹的是在携手走在太阳下的爱情故事。
梁白玉听着听着,睡着了。
这天傍晚,他纸飞机没折好就开始吐血,像是要把身体里的血全部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