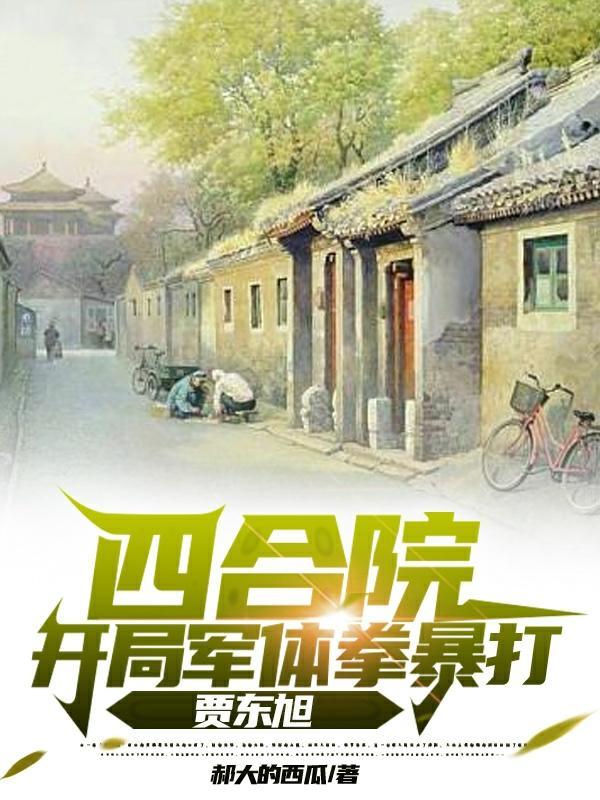UPU小说网>当城管遇到顽固小贩怎样办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邓绍疼的难受,撅着屁—股靠在厕所的门上,见我进来,这才伸手擦掉额头上的冷汗说:“你可回来了,你在不回来,我就死了。”
我挥挥手里的挂号本,问道:“不是让你在椅子上等我吗?你一个人跑厕所来干嘛?”
邓绍伸手指了指门外说:“急诊室那个孕妇,是我同事的媳妇儿,幸亏我刚才跑的快,不然可丢死人了。”
“可是……可是也不能就这么躲在这里啊,马上就要到你了。”
正说着,门外就响起了护士的叫喊声,分贝相当之高,喊的自然是邓绍的大名,那贯彻走廊的声音,让邓绍的脸色难看起来,迫于无奈,邓绍只好硬着头皮说:“走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不得不佩服邓绍乃铁铮铮的硬汉子,我搀扶着邓绍从厕所出去,意想不到的是,走廊并没有什么人,倒是护士很不耐烦的说了几句。
进了急诊室,我偷偷向门外瞥了一眼,见那孕妇以及家属都在隔壁的病房,这才安慰邓绍说:“你放心吧,他们好像没听到,咱们赶紧让医生看,看完咱们就回家,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邓绍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
医生进来的时候,看了我和邓绍一眼,说:“哪里不舒服?”
我扶着邓绍坐在医生对面,本想开口替邓绍把病情说了,以免他本人尴尬,可没想到邓绍却抢先一步说:“今天不小心划了一个口子。”邓绍指着身下,医生探头睨了一眼,点点头又说:“把裤子脱了,我看看。”
医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又对我说:“麻烦你把门关上。”
我急忙把门关好,回来的时候邓绍已经把裤子脱了,坐在一旁的床上,岔开腿说:“疼倒是不疼,只是走路磨的厉害。”
医生点点头,一面带上口罩和手套,弯腰在邓绍的命根子仔细检查了一番,大概是力气用的过大,邓绍疼的呲牙咧嘴。
医生看了一会,直起身子说:“还真够可以的,怎么弄的?伤在最里面的地方?”
邓绍憋的脸通红,时不时的瞥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责备,为了救赎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对着医生说:“是我一不小心咬的。”
“咬……咬的?”医生愣在原地,邓绍则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我会如实说了出来,大概在邓绍的心里,早已经把我骂个几千几万遍了。
“恩,我晚上不小心咬的。”
医生年纪不轻,大概这种事情也已司空见惯了,在惊讶过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摘了手套,坐在桌前提起钢笔龙飞凤舞的狂草一段,说:“伤口不大,按照上面的药方去开药,内服和外涂的分清楚,最重要的是不能沾水,夏天容易出汗,要勤换内衣,知道吗?”
我急忙接过本子,连连点头说:“知道了。”
医生见我一脸紧张,不禁带着笑意对我说:“小伙子,以后这种事情得注意,男人的命根子是最脆弱的,不能太用力,知道不?”
我十分后悔刚才自己把实话说了,还不如编个谎话糊弄过去呢,这倒好,让医生当成笑柄了。
出了急诊室,邓绍就忍不住给了我一脚,厉声道:“你小子是不是傻了,这种事情也能说实话?丢不丢人?”
我是个直肠子的人,有时候说话不经过大脑思考,我母亲就总说我是缺心眼。
邓绍见我低头不说话,叹了口气说:“行了,别杵着了,赶紧把药开了,我们回家,真被你折腾死了。”
我把邓绍扶到一旁的椅子上,随后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脉的速度跑了回来,邓绍看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这才关切道:“我又没逼你跑这么急,瞧你累的。”
我傻呵呵的笑了起来,说:“没事,早拿完药早回家。”
邓绍哭笑不得,抬手举在半空说:“小六子,摆驾回宫。”
鉴于邓绍有伤在身,我又不好做多责怪,只能委曲求全的笑道:“嗻,奴才恭迎皇上回宫。”
我作奴才样,把手垫在邓绍手下,邓绍却挥手打开了,笑道:“行了,叔真不舍得让你当奴才。”
我眯着眼睛傻呵呵的笑着,邓绍伸手在我脑袋上弹了一下,说:“折腾了一晚上,傻小子带叔去吃饭吧。”
我抬眼看了医院大厅顶端的大表,说:“这都几点了,哪里还有开业的地方?”
邓绍挑挑眉毛,笑道:“叔知道有一个地方不会关业。”
“在哪里?”
“走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
我撇撇嘴,以示内心的不忿,只能扶着邓绍一瘸一拐的出了医院。
“你说的就是这里吗?”我指着路边的摊位,烧烤的位置上浓烟滚滚,而路边的座位上,倒挤满了前来吃宵夜的人。
邓绍跛着腿,拉过马扎子坐了下来,笑道:“快点坐下,这家的烤脆骨特别好吃,说不定对你还有帮助呢。”
我不明所以,拉过马扎子坐下,说:“一个烤脆骨能对我有什么帮助?”
邓绍和老板点了很多烧烤,随后又点了半杯白酒,等酒上来后,才对我说:“烤脆骨只是用来吃的,我是让你学学人家做生意的精髓,懂不?”
我大致懂了,吃东西的时候,邓绍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老板闲聊着,例如什么几点出摊,几点收摊,住在哪里之类的,而老板倒也是个实诚人,滔滔不绝的说着,至于话里几分真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和邓绍也只是吸取有用的一部分。
“大海啊,全是水……毛驴啊,四条腿……”回到家里,邓绍由于酒精的作用,已经神志不清,嘴里念的更是搞笑的词句,我把他按在被子上,硬是扒了他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