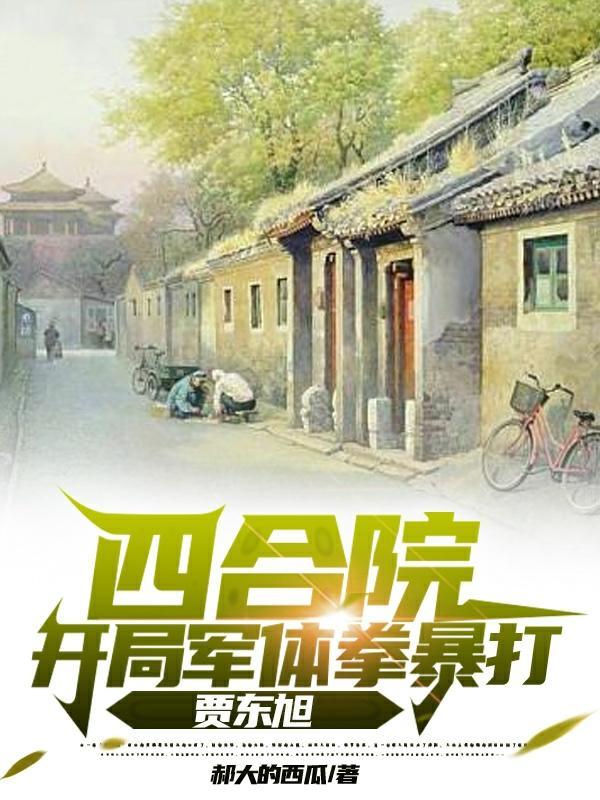UPU小说网>一帘风月闲是什么意思 > 63 公主来访(第1页)
63 公主来访(第1页)
夜寒烟回到住处的时候,天已向晚。
以她现在的处境,离开这样久而无人过问已是匪夷所思,而她前脚刚进门,后脚就有甘露殿的小太监过来传旨,这样的巧合更是让人不得不深思。
个中缘由,她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愿去细究而已。毕竟祁诺浔确实有他的为难之处,身为皇子,日日如履薄冰,若不能忍一时之苦,如何能在皇家生存下去?
监视她的几个老嬷嬷见她老老实实地接了旨,立刻便换了一副嘴脸。夜寒烟在房中听得她们一人一句“娘娘”长“娘娘”短,早已不胜其烦,她们几人兀自浑然不觉。
册妃礼定在下月初五,屈指算来也不过还有半个多月的日子,听说同日册封的还有一位秦婉仪,原是莳花馆的宫女。此外还有种种琐事,夜寒烟却半点都不关心。
自宫女一跃而成为四品宫嫔,这等际遇实在是闻所未闻,夜寒烟虽闭门不出,却也知外面早已流言如沸。
先时皇后曾大张旗鼓为皇帝选妃,最后却不了了之,个中缘由已经颇费思量;如今皇帝忽然亲自点了夜寒烟和秦素锦两人,简直就是将她们放在火上烤。一时之间,什么“祸国妖姬”,什么“狐媚惑主”,种种骂名,不一而足。
夜寒烟对宫中的这一阵骚动只作无见无闻,每日却也不作什么消遣,常常临窗一坐便是半日,嬷嬷们来逗她说话,她也听而不闻。这样过了数日,那些个老嬷嬷们终于开始担心起来。
这日夜寒烟照旧以手支颐,坐在窗前百无聊赖地看着院中那几株花木出神,却听见门外守着的老嬷嬷们齐声唱诺,似乎是外面来了贵客。
夜寒烟这一惊实在不小。虽知皇帝在正式册封之前不该来见她,但那老贼做事处处不依常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他做的还少吗?
看到来人时,夜寒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下虽仍然有些狐疑,却已像是重生过一回了。
莫云纤挥手将从人全部打发出去,笑吟吟地在夜寒烟对面坐下:“我来看看你。这几日闷坏了吧?”
夜寒烟随手倒了杯茶放在她面前,坦白地道:“闷是闷不死的。若能这样闷一辈子,我倒要谢天谢地了。”
莫云纤同情地轻叹一声:“你这是痴心妄想罢了。父皇费了多少工夫才得偿所愿,哪会舍得让你在这里闷着呢?我刚刚打外边过来的时候,看到柔仪殿和含英殿这两处地方宫人来来往往,着实热闹得很呢!想必不日便可以收拾出来,过两日你搬了进去,可就名正言顺是皇上的人了,这场是非,你到底还是躲不过的。”
夜寒烟听到“含英殿”几个字,微微一怔,已知皇帝的意思,心中不禁恨意更甚。
莫云纤却不知道这一层,只管感慨不已:“这世间的事,还真是谁都料不到。从前我见清哥哥对你关注太多,恨不得除了你才干净,谁知母后竟将你赏了浔哥哥;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父皇又来了这么一出。我真是想不明白,你一个小宫女有什么好,搞得这么多人为你神魂颠倒的!”
夜寒烟早习惯了她直来直去的性子,知她并无恶意,只得叹道:“什么颠倒不颠倒的,分明是因为我身份卑贱,好欺负罢了!”
“那倒也是。谁让你生了这样一张脸呢?你若是出身尊贵,就是倾城国色;偏偏你又没占个好出身,只好红颜薄命了!”莫云纤深有感触似的说。
夜寒烟不便与她辩解,只好苦笑道:“薄命也是命,那也没法子。不过你巴巴儿的跑来看我,应该不是来叹我薄命的吧?”
莫云纤却不答这句话,一双眼睛只管在夜寒烟的全身上上下下看个不休。
夜寒烟被她闹得心中惴惴不安,良久才勉强笑道:“这样看着我做什么?莫不是在盘算我这几根伶仃瘦骨适合清蒸还是爆炒?”
“我在看你这几根伶仃瘦骨是不是狐狸变的,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领?父皇都已经下了册封的旨意,竟还是有人敢对你念念不忘。”莫云纤抬起头来看着她的眼睛,半真半假地道。
夜寒烟心中一惊,慌忙笑道:“这话可不能乱说,我是不怕死的,可你好歹也要看在三殿下的份上,顾忌一点旁人的性命吧?”
莫云纤幽幽地叹道:“对你牵肠挂肚的人正是清哥哥自己,你要我看在他的面子上放过谁呢?”
“公主,这话可是不能乱说的。”夜寒烟吃了一惊,下意识地道。
“希望是我乱说,”莫云纤冷笑道,“可是我每次乱说,好像都会很准的。我本不想来看你,可是清哥哥三番五次求我,倒叫我推脱不得。”
夜寒烟的胸中不受控制地砰砰乱跳起来。
她以为除了祁诺浔,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以她为意,可是莫云纤又万万没有欺骗她的理由啊!
祁诺清,他不是分明不在意她吗?他若是当真有心,何必等到如今?
夜寒烟好容易才压下心中的满腹疑团,竭力装作平静地追问道:“三殿下叫您来看我?这可奇了!我记得我虽然性子可恶了点,跟三殿下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啊!这个时候,他该犯不着来落井下石才对吧?”
“你呀,口是心非!”莫云纤带着几分无奈叹道。
夜寒烟觉得双颊烫得厉害,心知此刻自己脸上一定红得像火,为了怕莫云纤追问,只得深深地埋下头去。
莫云纤早已看见她神色有异,却只装作不见,继续道:“你心中何尝不知清哥哥也是在意你的。他只是性情孤傲,不肯示弱罢了。这次我来,是替清哥哥传一句话,他叫你时时记着,人若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就这一句话?”夜寒烟诧异地抬起头来。
“这还不够吗?你都要做皇妃了,他还是放不下你,时时惦记着怕你想不开,你还要怎样?人人都以为你如今一步登天,心里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却知你心中煎熬痛苦,这份知心,还不难得吗?”莫云纤的声音有些冷。
夜寒烟心中惊慌失措,只得胡乱辩解一通,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辩解的。
莫云纤面无表情地看了她许久,才垂首低声叹道:“清哥哥是个糊涂人,你也是,我又何尝不是?如今看来倒只有浔哥哥一个人活得明白,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