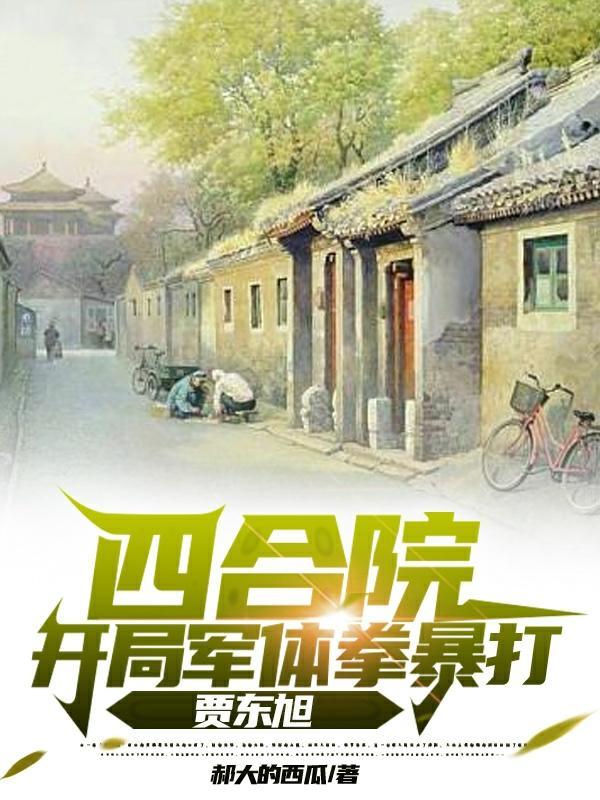UPU小说网>人鱼的诅咒漫画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小女孩才喜欢这个。”艾格道,“我不喜欢……至少现在不喜欢。也不太喜欢意外,我的意思是……”他摸到了掌心下的眼皮,感到紧闭的眼睛终于睁开了,“看到那仅剩的一艘船了吗?你得把潘多拉号留一下,比起游回加兰岛,我更喜欢坐船回去。”
“那座岛……加兰。”
“对,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家乡。最重要的是——”艾格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从来不曾确定的可能性,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大海漫无边际,一艘船从岛屿的远行都可能是永别,更何况是一个女孩。
唯一确定的是,当幸存者推开门,找遍每一个角落,岛屿上始终没有出现过一株代表女孩的红珊瑚。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失散之人,可以成为她在茫茫大海上指引迷途的灯塔,那一定是重现的故土,那唯一的、共同的归途。
“最重要的是,安洁莉卡……你记得吗?”
“记得……女孩。”人鱼说,“海鸥。”
“……海鸥。”艾格重复。
说话间他已经顺着手底脸庞的轮廓,再次摸到了耳鳃的根部,现两片长长的鳃又被藏进了间。他想到了溶洞外的那张最为接近人类的面孔,于是把长鳃从纠缠的间找出,捏起最顶端的骨刺,拉开,展平,就像在展平一片自己衣角的褶皱。
手指轻轻弹了弹,有水珠从鳃尖落了下来。
“是的,海鸥。”他说,目光的方向也来到了这片鳃尖,“如果她见到一条人鱼,尖叫估计能把船顶掀翻。想想看她该有多快活?证明了一个传说,从此再也不会愁自己在吹牛大会的头筹。不用怀疑,她会用一整箱宝石来交换一条人鱼朋友的名字,嗯——”
他停顿,有笑容在那张脸上一闪而逝,“当然,我会用十箱。”
最闪耀的宝石最易碎,最美丽的神情也最短暂。那颠倒的、失去知觉的世界却在这短暂的神情里终于苏醒过来。意志回归躯体,靠近全由本能,人鱼直直望去头顶。
被这一瞬间召唤回来的还有那最初的疑问——什么时候他不会恐惧?那么,他就该钻出海面,试一试习得的礼节,送上一些人类喜好里的东西……从银鲑鱼开始。
他会笑吗?
一条不够,得一群。
天好像有点放晴了。
艾格抬起头,现衣服半干,寒冷已经远离,风吹过来的时候不算温暖,却也不像之前那么刺骨了。
北海的太阳很少曝晒,通常远而清冷。算算时间,也许该到黄昏。
“落日出现了吗?”等到稍也干透,他问起这里唯一的一双眼睛。
“……出现了。”
耳畔的声音像从很远出现,也许是因为此时风声无垠,但鱼尾和躯体的重新贴近却很鲜明。
小腿和靴子还在被拍岸的海浪时不时溅湿,接着那条腿被鱼尾捞起,推往更高处。艾格收回腿,换了个坐姿,想和他商量回船的事情,却意识到这好像是时隔多年,北海的第一个落日。又想,看完落日也不迟。
“现在的太阳是什么颜色?”
“……红色。”
呼吸在脸上,直直的。艾格拨了拨他的脸,“向西看,太阳在那边。”
“浅一点的……红色。”
“也可以叫橘红。”
“橘红。”
声音在不假思索重复,与此同时,是一双缓慢伸过来的蹼掌。人鱼捧住掌心的脸,指腹停留于红珊瑚的眼角。接着,手指向耳后滑去,从后颈到脊背的一个抚摸,拥抱轻而潮湿。他把他的脊背收进手臂,脸颊藏进颈窝。
“……橘红……你会看见,重新看见。一定。”
蹼掌稳稳停在了肩膀处,底下的黑鳞却还在时不时颤动。与其说那双手臂是在进行安抚,不如说它终于找到了能平静安放的地方,艾格没有挣脱。在逐渐习惯的黑暗里,大海的围绕中,再没其他东西比这个冰凉的拥抱更具体了。
“那么,希望我重新看见的第一天可别是个坏天气。”他同样拍了拍他的后脑勺,“天快黑了,你带我去岸边?船上的人找不到这里。”
应该点头,应该说好,但落日还没彻底消失,落日之后还有月出。北海的日光从不曝晒,一部分的躯体却还在灼热作痛,只有海里的动物知道那种疼痛永远不会消失,而人类再也不该被暴露在外面的世界。哪怕这也成为了一件需要时时质疑的事,鱼尾能否完全隔断波涛汹涌的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