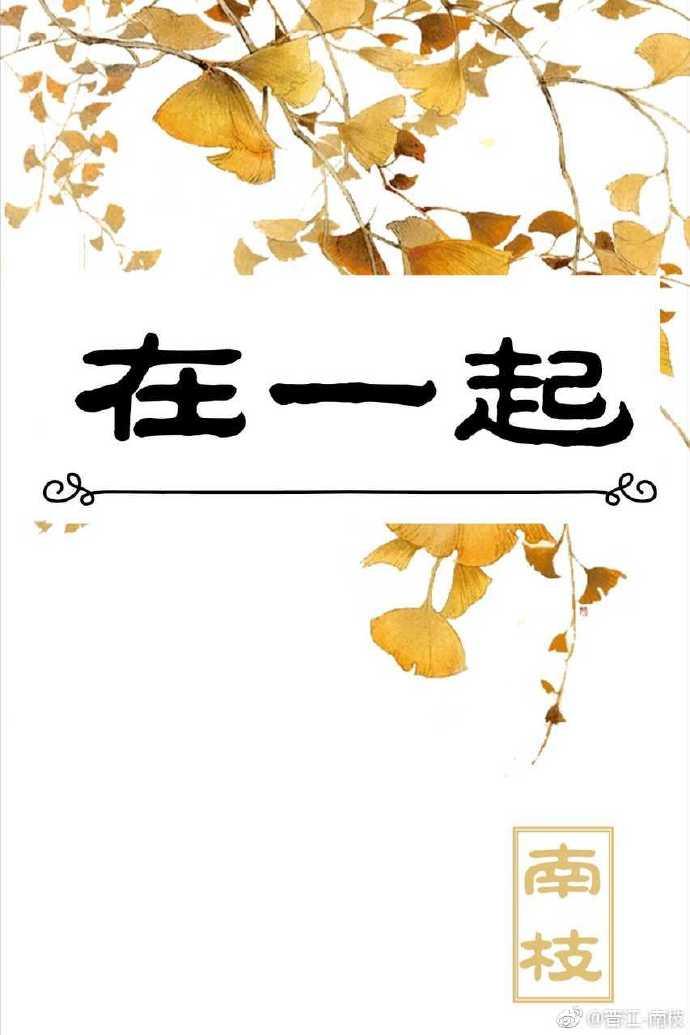UPU小说网>樱桃痣怎么治 > 第63頁(第1页)
第63頁(第1页)
殷時嫌的語氣寬縱又無奈,"知道自己命好就再聽話一點,多在家裡待著陪我,別一天到晚滿世界的玩。看韓家那丫頭,成績比你好就算了,德藝體美哪個都沒落下。"
"小鈴是優秀,我不如她的啦。"殷姚嘿嘿一笑,放下手裡盤亂了的狗狗,轉過頭,和所有閒來無事玩笑哄鬧的孩子一樣,明明知道答案,卻還是假模假樣地問,"媽﹣﹣我要不是你親生的,你還會這麼疼我嗎。"
殷時嫌的表情和從前一樣,只是眼裡的筆音消失了,但也只是很短的一瞬。她習慣性勾起的唇角弧度加深,將眼睛眯了起來,像是藏起了思緒。"會的。"
只是一句類似撒嬌的閒話,殷姚並沒有將此放在心上。
被愛大的孩子總是懵懂又柔軟,像腿邊繞來繞去的小狗,和絨毛厚實的地毯。還有母親豐腴的皮膚,撫摸他額頭的掌心稍微有些濕熱,卻讓人安心又舒適。
當背部狠狠撞擊上床墊的時候,再輕彈的脂棉也會變得堅硬。
從什麼時候起,床不再那麼柔軟了。一次又一次,被用粗暴的力度像塊破布一樣地被扔到床上,殷姚抗拒地扭過頭不去看他,咬著唇逃下床,雙腿慌亂地踩在地上,腳心被酒店的地毯扎得生痛。
他又一次被扯了回去,額上沾了汗的髮絲凌亂不堪,這一次他是以趴著的姿勢,後頸被掐著,臉埋在被子裡,哭紅了眼,不安分地掙扎,"不要,我現在不想……別拉我,疼……好疼!"總覺得,就算有身量差異,都是成年人,也不至於推都推不開他。但殷姚怎麼也沒想到自己身體差到了這個地步,從包間一路上折騰到房間,體力被消耗的乾乾淨淨。
起初是抗拒的,陳韓峰惋惜又複雜的眼神讓他尷尬,付矜垣玩味直白的目光讓他羞恥,酒桌上直白的調笑令他無地自容。
殷姚的拒絕比暮死的蜂鳴還要微弱,政遲也並沒有和他膠著多久,就在電梯裡他哭著說要回家的時候,政遲就把他按在玻璃上惡狠狠地咬他。
耳朵,嘴唇,脖子,手腕。
讓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快肉,被這瘋了一樣的人噬來,於齒間細細地撕磨嚼碎,嚼爛了再吞下去。
"不要……咬我了……!嗚……"後頸處的軟肉被他銜在嘴裡,吐息潰熱,像燒透他的河火。
因為是他的氣息,是喜歡的人的氣息。
"為什麼逃。"政遲手握著殷姚細瘦的腰,將他牢牢地扣在掌中。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欣然適應了殷姚愈發清瘦的身體,自有那輕盈的味,配合著無與倫比的乖順,愈發像他藏品櫃中精美的瓷偶,深得他心意。
他這也漂亮,那也漂亮。
鮮活時是美的,虛弱時也令人驚嘆。終有一天,他因為自己完全碎掉,心和身體一樣殘破衰敗,他的美麗也不會因此削弱消失。
不會消失,不會離開他,死去後也是被鋒釘鎮於匣中的標本。
是他的。
是他的,是他的沒錯。
政遲啃噬他的力道變輕了,就那麼詭異地變成舔吻,力道溫柔得令人戰慄,他吮去皮膚上的血珠,凹陷的齒痕紅艷無比,淤血堆積在薄薄的皮膚下面,幾天後就會青紫斑駁。
"姚姚……"
般姚心臟就緊縮,想捂住耳朵,不想聽見。自從那天開了頭,政遲在做愛的時候總是這麼叫他。
舌黏著上顎,又是只是輕飄飄的氣音,像是嘆出的兩個字。
靡醉時邊吻邊喚他,或是深插在滑軟吸緊的深處,每叫一聲,殷姚就無法抑制地縮緊,絞得他笑罵自己是妖精,又被狠重的楔進深處,撐得小腹隆起,恥人的快感讓他除了哭著求饒和叫床再說不出一句話。
殷姚搖頭不去看他,臉埋在被自己就算是呼吸不暢也不願意轉過來,帶著鼻音
悶地央求道,"不要叫了……"
在叫誰啊。
不要叫了。
什麼姚姚啊.。。。
政遲沒用多少力氣就將殷姚翻了過來,見人還是閉著眼不願意去看他,就去啄吻殷姚哭紅了的眼皮和鼻尖,他吻的虔誠又痴迷,惡劣且卑鄙,用幾乎是用愛撫的力道剝去殷姚的襯衣,俯視時的眼神比泥潭還要髒污混沌。
多漂亮。
殷姚像一團柔軟的脂肉,水津津地盛在被褥中,半化不化地輕喘,哭腔黏膩,被把玩到迷亂。
許是也有攝入酒精的緣故,乳尖鎖骨肚臍都是鮮粉的,他看起來愈發像食物。
在耳廓邊粗重的喘息讓殷姚重重地打了個激靈,揪緊身下的被子,雙腿在不經意間悄悄絞緊,換來他帶有濃厚興味的悶笑。
殷姚攔著他分開雙腿的手,"我不想要……"
"至少不要在這種時候攪擾我的興致。"政遲的指腹並不算溫柔地剮蹭殷姚半翹的陰莖,沒怎麼使用過的嫩色也布有細弱的血管,和它的主人一起被控制,每一次不輕不重的揉擠都讓殷姚驟顫,嘲笑道,"不是想讓我別為難人嗎,順著我心意不是更有求人的態度?"
殷姚聞之一震,瞪大了雙眼看著他,眼睛更紅,嗓音嘶啞,久久,才輕聲問他,"你把我當什麼呢……"
這副半碎不碎被傷透了心的樣子,亦是他喜歡的。
政遲撫摸著殷姚的臉頰,語氣可謂縱溺,像戀人溫存時的愛哄,他低笑一聲,"男娼,婊子,或是,或都不是。無論你怎麼想都可以。姚姚,你覺得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