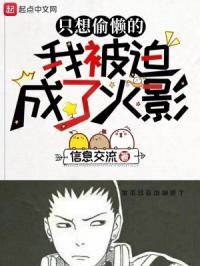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小狗歌完整版 > 第1章(第2页)
第1章(第2页)
于是程斯刻十岁以前的童年就在一方昏暗的老屋内,伴着锁链的铁锈味与白粉的刺鼻味迷迷沉沉地度日如年。
程斯刻动了动自己睡僵了的四肢,缓缓从地上爬起来。他无言盯着靳柔的后脑勺看了一会,肚子出咕的一声,他低头用脑袋顶了顶靳柔的后背。
靳柔今天睡得真沉,这样也叫不醒她。
程斯刻向前俯身,用牙齿轻轻咬了咬靳柔无力垂在侧腰上的右手。
靳柔的手骨瘦如柴,上面布满凸起的血管,但程斯刻还是能从他妈的手上感受到一股子温暖和柔软。
但今儿个,靳柔的手很凉,很冰,甚至,不似以往软和。
程斯刻有些疑惑,他的黑眼珠动了动,用比刚才稍大一些的力气咬了咬靳柔,这次他没使好劲道,嘴一不小心一扯,靳柔的手径直掉落在背后的床褥上。
如果程斯刻再大一点,明白了死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也许就不会因为叫不醒靳柔,而一遍一遍咬着他妈的右手。
可惜被锁在床头将近七年的孩子什么都还来不及懂得,母亲就猝然离世了。
程斯刻因为靳柔的毫无反应而越焦躁,他开始用劲儿,咬不够用扯,扯不够用撕。
他一边咬,嘴里一边出困兽一般的低吼,直到他妈的右手几乎被他咬的血肉模糊没了样子,直到有村里的邻居恰好有事儿来找靳柔,被程斯刻如食人恶鬼一般的疯癫模样吓得瘫倒在地失声尖叫。
之后的几日,周边的邻居帮靳柔草草办了后事,而程斯刻吃母亲尸体的事儿也被传得人尽皆知。
同情终究抵不过恐惧,程斯刻被留在老屋里,只偶尔有好心的老汉给送来些吃食。
老汉每次来给程斯刻送饭,都能看着这孩子麻木地将自己锁在床头,夕阳斜切,但那一缕红光却再也照不到程斯刻的脸上。
老汉跟放狗食一样将碗放在程斯刻面前的地上,转身蹒跚着踱步出门,嘴里念念有词:“造孽,造孽啊。”
三个月后。
温浅斜靠在一辆迈巴赫Vs68o的后座,隔着一层黑色的纱帘无言望着窗外越来越原始和自然的风景。
夕阳残照之际,群山开始映入眼帘,明明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万物都该是生机勃勃的。但或许景随心动,他内心怆然,衬得这红光下满山的新绿也显得苍凉落寞了不少。
他其实脑袋有些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有时候想到了印之遥,有时候想到了他父亲温晏,有时候又想到了他的小狗,一只养了十五年的伯恩山,两个月前寿终正寝离开了他。
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心脏闷闷的始终难受着。
前头司机看温浅一路上都没开口说话,便搭话道:“温先生,您可以把纱帘拉开,这边景色还是很不错的。”
温浅用手感受了一下还有些余温的残阳,轻轻摇了摇头,清润地嗓子缓缓开口:“不了,我不喜欢太阳。”
司机看了一眼几乎快要沉入地平线只剩了个头的残阳,又看了看温浅白的跟瓷一般的肌肤,心道这人怕不是从未晒过太阳吧。
进山的路有些颠簸,温浅不晕车,但被颠得难受。这一趟旅程对他来说算是一件极苦的差事,先要乘飞机从南淮飞到千里之外的平光,再从机场坐车一路进到下面镇子边缘的山里。
虽然钟宥齐生怕累着他,早就给他从分公司派了一辆迈巴赫七座等候在机场,但温浅向来娇气得不行,即便这般他还是觉得累得够呛。
钟宥齐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哥哥,他、钟宥齐再加上印之遥,三人曾经亲密无间。
钟宥齐大他五岁,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待,很照顾他。
说起钟宥齐,这人的电话便打来了。
“快到了吗?”温浅听见钟宥齐再那头问道。
温浅被颠得有些想吐,他强压住自己的不适开口:“嗯,看到山了,应该不远了。”
“我当时就说把伯父和小狗的骨灰就留在南淮,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下葬了最合适,送一趟不够你这小身板折腾的。”钟宥齐语气中带着谴责,还是心疼温浅。
“我爸这一辈子也没跟我说过两句话,临了让律师转托我,让我送他的骨灰回乡安葬,我再不孝,这点遗愿还是替他完成了吧,省得老头子整天来梦里找我麻烦。”温浅垂下眼眸,掩饰过眼里的情绪,虽然根本没人在看他。
“行吧。”钟宥齐知道现在说什么都迟了,人都快到地方了,遂转了个话题,“你的祖屋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全部翻新装修完了,完全按照你要求的风格设计的,你待会儿去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温浅的娇气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兵马还未动,装修要先行。早三个月温浅就跟钟宥齐说了想要来这边山里住老屋的事儿,请钟宥齐帮忙把老屋从头到脚全部装修翻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