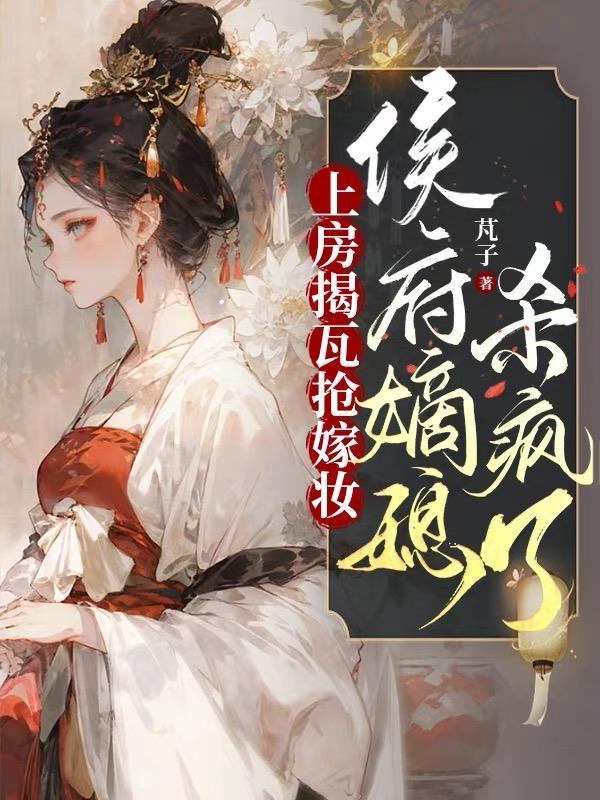UPU小说网>贰心臣免费观看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那两个小身体同样被我放上了龙榻,我再次把帘子放了下来。
不一会儿,太后过来了,一路有人语,好像还沉浸在宴会的气氛里,我却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宴会那会儿,恍若隔世。
听见裴公公在外面道:“太后娘娘,皇上吩咐,这是要事。”
于是太后的声音说道,“李德全,喜儿,你们两个就在外面侯着吧。”
我垂眼盯着地板,最先进入我视线的是一双精致的暗色绣花鞋。
我微微地笑了,抬眼对上太后的有些孤疑的面庞。
看见我一个人在屏风外站着,太后道:“五儿,皇上呢?”看着她的眼光扫过焚香的熏笼,扫过雕花的八角花瓶,扫过刻有名山大川的屏风,最后注视在我的脸上。
我双膝一曲,跪在了她的面前,我道:“母后,孩儿犯错,还请母后谅解。”
太后上下打量了我,皱了皱眉,疑惑道:“再怎么闹腾,能有什么大错?”
我点了点头起身,变换了表情,目光炯炯地看着太后,我轻轻地道:“母后,孩儿要当皇上了……”
太后闻言,连脸上的皱纹都僵硬了,凤目圆瞪。
“你……你……”她一脸震惊,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她抖着嘴唇,向屏风里面冲过去。
然后她钉在那里了。屏风后面虽然还有床帏,但那么多血迹,我来不及一一擦干净。
太后也该是见过风浪的人。
太后剧烈地呼吸,扶住了屏风,她转头看我,凤目尽红,眼中血气弥漫。她的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的身上,我平静地回视她,却见她忽然身体一阵痉挛,几乎要倒地,我忙抢过去扶住。她靠在我的怀里,目光没有焦距,喉咙里发出一阵暗哑不明的呜咽,容貌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年。
忽然她全身一抖,推开了我。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她原本保养得当的圆润的声音已经嘶哑了,她原本娴静从容的泰然如今早已不复存杂,我面色平静,目光迎上她狰狞的面庞。
一掌剐了下来,她手上带有首饰,牵动了我的面皮,刮出血来。我的头偏向一边。再抬目,我静静地看她,慢条斯理地道:“这一辈里除了我,亦有皇室支脉,只是离得远些,已隔了三代以上,端看母后怎么抉择了。”
瑞兽吐烟,裴公公已经点了一盏香炉在房里,青烟漫漫地一点一点弥漫出来,好像要荡漾开殿里微微血腥的味道。
太后站在那里,一直没有言语。
等再开口的时候,她只是用她暗哑的声音缓缓地道:“五儿……五儿……我和皇上,都错看了你……你,现在给我跪下。”
我依言跪下。
太后凤目仍是布满了血丝,她死死地盯着我,盯了半晌,她哑声道:“既然做了,就得对的起这个位置,做好。”
太后的声音低沉,在大殿中回荡,
我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一个头,沉声道:“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太后点点头,目光犀利冰寒,她转向裴公公道:“裴永,你也是新皇的功臣了,现在哀家让你去做一件事。”
说罢,太后将腰间的挂坠取下来,交到裴公公手里:“你这就去交给禁军统领文泰,今夜刺客横行皇宫重地,让他带禁军兵士急行过来,七万驻皇城各个要口通路,各家各户非圣旨不得出门,以防刺客逃窜,违令者比刺客同谋,斩;余下一万,守卫皇宫。同时,令其另派人马,走高家大宅,将高宇的妻女儿小都送到皇宫里来。不得有误。”
“遵懿旨。”裴公公一个躬身,接令去了。
我站在太后的身后,她的背影显得清越而坚强。
“喜儿!李德全!”太后高声道。
一个大宫女模样的人和太后的贴身太监进殿拜伏,太后从怀中取出一枚玄铁令递在喜儿手里,冷声道:“即刻出京,近畿地区有驻扎的高家铁羽两万。你和高将军也算有一面之缘,你带着这枚令交予高将军,就说是哀家说的,让他无论是谁的诏令,都按兵不动,哀家自会护他家小周全。”
“李德全,传懿旨,刺客尚在,立封皇宫,各宫主子于自己宫内歇息,不得出门,不得交头接耳,不得私自窜行,违令者作刺客同谋,斩!”
“是。”
当大殿重新空荡起来的时候,太后看着殿门的方向,久久没有说话。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太后,有这样的皇帝,有这样的王爷,有这样的朝廷,我今日才敢用此种方式放手一搏。若是时运不济,其中一项不成,如今我已早入黄泉。
我从太后的背后,轻轻地执起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我将她牵到了屏风后龙榻的旁边,我道:“母后,您深吸一口气,儿子要把这帘子挑开了。”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房里昏黄的烛光摇曳,照在太后艳丽不再却端庄的五官上,看不清的表情,她的唇抖一会儿,等停了的时候,已不知过去了多久,她声音暗哑:“五儿,你就挑开吧,母后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看着她逐渐老去的侧脸,我心下诧异,沉声道:“好。”
便伸手将帘子挑开,太后向大鸟一样一下子扑在了皇帝身上,无声地啜泣起来,身体剧烈的起伏。
她用她自己起了皱纹的手指一点点摸搓着已经苍白的皇帝的脸颊,我从后面轻轻地拍着她,她脆弱的身体让我有一丝错觉,她在这一刻好像不是太后,而是一个寻常的老太太。
禁军,泛着暗色的铠甲像潮水一般涌至皇城内门。绣着天龙卫的金边的旗帜在黑甲前烈烈的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