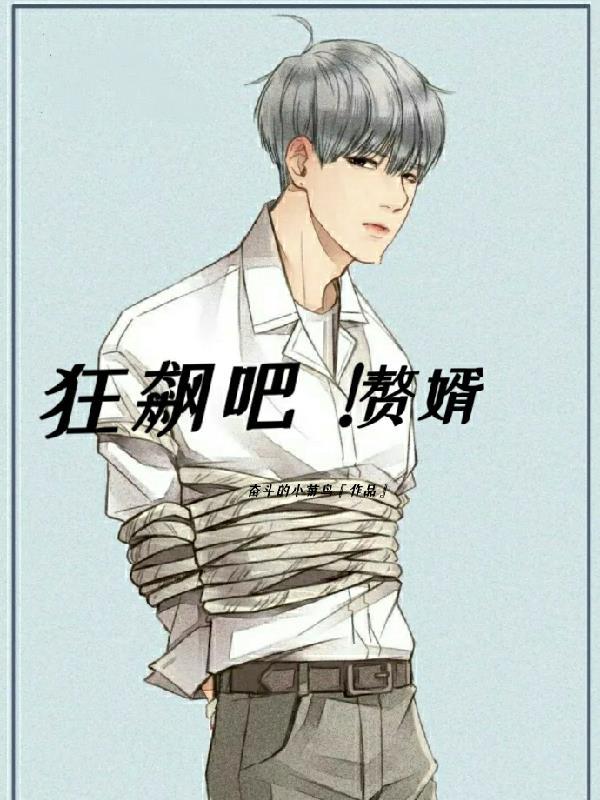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狗尾巴草编织小狗 > 分卷阅读8(第1页)
分卷阅读8(第1页)
把粥吃完了。
王百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一直看着他,等他吃完了,温声道:“快休息吧。”
孟归南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晚上躺在床上几乎要不了几分钟就会昏睡过去,但每月的这一天晚上,他总会失眠。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过去,一会儿思考未来,但更多的时候,他都在盘算那一长串儿的欠款什么时候可以还完。
不知道几点钟睡着的,还不到八点,他就醒了过来。
慢吞吞地洗漱,穿衣,吃饭。
出了门,他和王百琴一路沉默着坐上了开往郊区的公交车。
来得有些晚,他们是最后一个号。
王百琴对会见的流程烂熟于心,提前准备了食物,两人坐在等候区吃完了午饭,又等到下午,才轮到他们。
和上个月见到孟良一样,他说一切都好。
孟归南看着他的白,舌根泛着极重的酸苦,他想说在监狱里怎么会好,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我们也挺好。”
孟良话不多,基本上都是孟归南和王百琴在说,他静默地听着。
他坐在玻璃另一侧的塑料凳子上,身上穿着监狱里统一放的蓝色囚服,肩背佝偻,握着听筒的那只手骨节嶙峋,扭曲的青色血管在干枯的皮肤下清晰可见。
记忆里那个总是笑呵呵,精气神十足的孟良已经消失很久了。几年牢狱,如今他脸上的每道褶皱都在诉说活着是一件多么煎熬的事。
“爸,我和妈盼着你呢。”孟归南试图让孟良燃起些生活的希望来,孟良抽了抽嘴角,扯着嘶哑的声音回道:“是我拖累了你们,你们别再管我了。”
王百琴附在一旁听见孟良的这句话后,抢过听筒,死死瞪着玻璃那侧的孟良,咬着牙道:“你说别管你了?你知道这五年来小南……”
“小南怎么了?”孟良紧张地瞪着眼,手掌扒在玻璃上。
“妈!”孟归南想阻止王百琴继续说下去,又怕动作过大引来注意,只好用力从她手里把听筒夺回来:“我没事儿,就是医院工作太忙了,总睡不好觉。”
孟良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听他聊起工作,提起了一点精神:“生命所系,医生的责任是很重的。要多锻炼,这么大的压力要有个好身体才行。”
“我知道了。”孟归南点头,过了几秒钟,他又说,“爸,无论是哪个债,都有还完的一天。”
孟归南每个月都来,这句话每个月都要说一遍,他无比希望孟良也能像他一样站起来,坦然地接受人生里突降的厄运。
但苍白的话语似乎无法改变孟良心中人死债消的极端想法,孟归南次次说,他整个人看上去还是一潭死水。
一扇玻璃将这个家隔得支离破碎,孟归南闭了闭眼,把那些压在心头重逾千斤的情绪摁了下去:“人么,只要能喘气儿,就有活路走,重要的是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
“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什么都会过去的。”孟归南强调道。
那场打击对这个一辈子都温和善良的男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泪水逐渐淹没了那双浑浊的眼珠,过了很久,他垂着头小声说道:“对不起。”
孟归南看着孟良,有时会觉得他很懦弱。
父母是孩子一辈子的老师,孟归南从小到大在孟良身上学到了很多,而最后一样是孟良没有的勇敢和坚强。
回程路上,母子两人依旧是一路沉默。无论是孟归南还是王百琴,都要靠着这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各自收拾心情,回了家,他们都得振奋精神,把日子继续过下去。-
孟归南在晚间六点四十分到达菡雨楼,一晚上他都心不在焉。3o1的酒水送到了3o7,明明3o2点的餐食,却让人送到了312。
李乔趁得空倒了杯热茶递给他:“南哥,你咋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