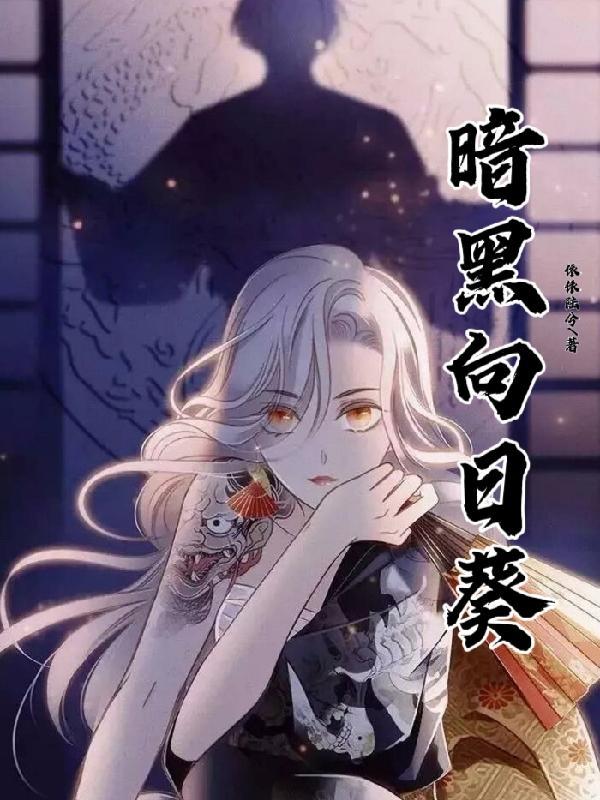UPU小说网>浮生之殷商风流90最新章节免费阅读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他只是将头埋得更加低了不在作声,南仲与子眛曾在大商被世人所看好,郎才女貌有着绝配一说,臣民皆看好这一段姻缘,可是谁又知道造化弄人。
而将子眛扔向西岐的罪魁祸首竟然就是南仲,将心爱之人拱手让于他人,谁又会信会是因为天下大义,只会道是那南仲大将军变了心,做了负心汉罢了,岂不叫天下女子为这样一个美男子寒了心。
子眛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侧着身子看着低下头的南仲,身后替她挽裙的侍女都为她感到不值,上将军南仲竟是这样一个负心之人。祭坛上巫师还在等候,这一幕让在场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大臣们一个个的摇着头。众说纷纭,南仲与子昧之事,大商臣民皆知。
也许过了很久,也许没有多久,等不到回答又在这种地方她还能做什么呢。自己的王兄还在高台上等,没有催促,王兄至少还是疼自己的,她又怎么能为了一己私心而至大商于不顾。
“大王,您真要把子眛远嫁西岐吗,那南仲”
“寡人也不知道为何,南仲执意要如此,眼下木已成舟,寡人是天子亦不能出尔反尔。”
南仲对子眛的情,自己作为王兄,又和南仲在幼时是结拜的兄弟他怎么会不知道二人的情意。
若南仲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那么帝乙又如何会将军事大权托给他。
二人皆有意,而自己也准备在南仲及冠之年将子眛许配给他,可是没想到大商生了这样的祸端,要让自己的妹妹去和解。
送出子眛却是那个深爱着她的人,帝乙虽然是君王,君王寡爱,但他并非不懂,只是身不由己罢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世人所想看到的,亦是帝乙所希望看到的。
子眛登顶,众臣皆跪拜下来,南仲更是,自祭祀开始他便一直低着头,他深知今日盛装的子媚是极美的,他能想象到。
巫师在念完密密麻麻的话语后从祭坛上拿出一块龟甲,那是事先准备好的,龟甲背面凿着小洞,这些洞是人为,是帝乙私下命那些巫师们准备的。
“跪-天父。”
于是一旁的帝乙与子眛及祭坛下方的众臣皆跪拜。
今日若无差错,子眛的婚期与行程就在小公子的百日之后。
呲--咧--啪--塔。龟甲裂开的声音充斥着台顶,玄鸟图的黑色大旗再空中飘扬着,帝乙亦不为所动,子眛也不紧张,因为一切皆是定数。
或许,若今日卦象为凶,她便可以不用出嫁西岐。她该祈求是凶卦。但是她并没有这样想,因为她知道今日,不过是走个形式给大商臣民们看罢了。
况且,这是南仲所求,她心已死,嫁到哪去又有什么差别呢。
领头的大巫师从火中将那烧的裂开的龟甲取出。
将它放入饕餮纹盘之上;本来是要照着甲骨的裂纹来念凶吉的,事先做了手脚,那么这一定是吉兆,但是也会有出差错的时候,不过因是替君王办事,巫师们小心的很,故而极少出差错。“王上!”
大巫师战战兢兢的在俯首的帝乙耳旁说道。
帝乙大惊,睁开眼起身看着盘中的龟甲。
大商自开国,占卜便为日常之事,龟裂的横纹长则为凶,短为凶,横纹穿过竖纹也为凶。
龟甲断裂刚刚好,横纹及其短,又穿插在竖纹中间,错综复杂。
帝乙呆愣,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该如何决断。子眛出嫁,已经是定局,但是这是天命吗,连天父都要阻止。
祭坛下,百官低着头,因为巫师未曾喊起,信鬼神的商人亦不敢抬头窥探天机。
帝乙俯下头看着跪在祭坛中央的胞妹,皱着浓眉;“眛儿,寡人再问你一句,可愿嫁否。”
“臣妹乃王上胞妹,如今大商有难,臣妹怎敢为一己之私。”
这话说的让帝乙都有些惭愧了,“按之前的说吧。”
大巫师自然明白,还是按之前的说辞,只是这龟甲下来时肯定是要更换的。
“天父甚喜,以降横纹,是为大吉。”随后提了提嗓子;“起!”
那一声大吉,深深的刺痛着南仲的心,此时,怕他是比子眛更加难受的那一人。
“天佑大商!”
“南师长,南师长,该起来了。”将南仲从恍恍惚惚中拉回的是虞起,是多亚,武官之首的副职,南仲的官职是亚,即武官之首。
“南师长,您这是何必呢。”虞起年长南仲十岁,是从战场上血杀到如今地位的,一直跟着南仲出生入死,他尤为尊敬这个小他如此多的师长,起初是瞧不起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的,而这些年南仲军事上的本事是让他不得不佩服的。
南仲用着爽朗的一笑而回答了他的问话,意在他无需为自己担心,也意在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更意在他不后悔。
但是那笑很快沉入海底,剩下的依旧是那张俊俏肃穆的脸。世人常传,大商的师长上将军,是个不会笑的人,可正是那严肃,为那白净的脸增添了几分英俊。极少人见过南仲的笑容,虞起见过,那是在提到王女子眛时,上将军开怀之笑。子眛也见过,那是在自己眼前之时。
临了要退场,是由帝乙先行离开,在接着是子眛,最后才是百官。
此时众人是站起来的,帝乙从身边略过,只需微微行礼即可,帝乙略过南仲时,特意侧身瞧了瞧。
一声长叹,表着帝乙的无奈,更表着君王的质问;何故如此?
南仲只得双手合起,将腰躬的越发下了,直至宽大的袖子将自己遮掩住。帝乙离开,南仲方才放下手直起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