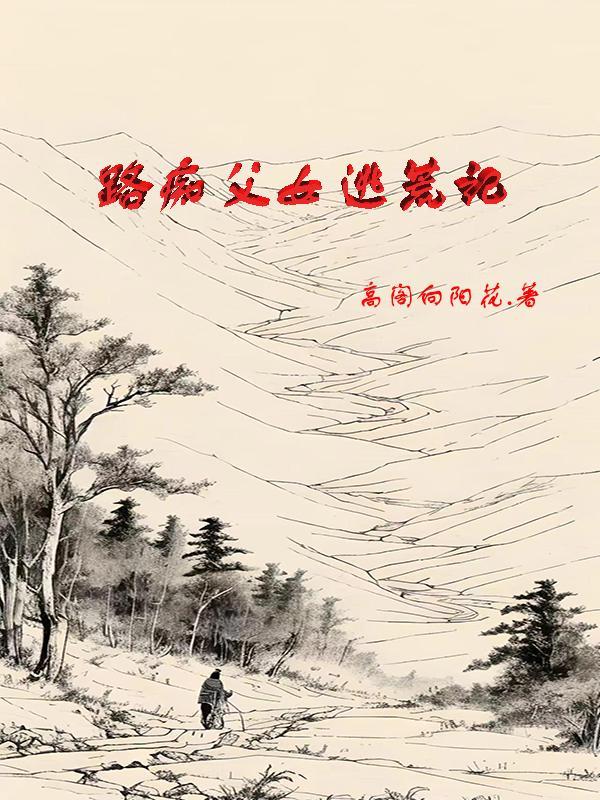UPU小说网>短剧浮华梦 > 第七十八章 塞翁失马(第1页)
第七十八章 塞翁失马(第1页)
“次卿,皇曾孙。”许广汉醉眼惺忪,喃喃道,“我年轻时是昌邑王的郎官,跟在藩王身后,出行骑的都是高头大马,神气到不行!“
刘病已眉眼都眯起来,笑道:“我知道。”
“你真的知道?”许广汉人都醉得伏在案上,转而抬起头,“酒呢?怎么还不快摆酒上来。”
刘病已饮一口酒,却将他的耳杯收了起来:“我小时候在史家住过一段时间,鲁国离昌邑很近。“
摸不到酒,许广汉也不恼,眼神迷离起来:“那时候我是昌邑王郎,张贺是太子舍人。昌邑王的舅父想让昌邑王争太子,张贺忠心护主受蛊巫牵连,还是他弟弟张安世去跟孝武帝求情才将死罪改为宫刑。
那时候,我们分属不同的政党,各自为营。可居然有一天,我也会因为从行而盗受宫刑成了张公的下属,和卫太子的孙儿结亲!这事,还是掖庭令先与我说的,要将平君嫁给你。
兜兜转转一大圈,太子、昌邑王都输了,继位的是小儿子孝昭帝。可是孝昭皇帝没儿子,做了大将军一辈子的傀儡,同样也没有赢。“
“是很神奇。“刘病已点评,“卫太子、昌邑王、孝昭帝都输了,甚至连刘贺也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退了场。”
“二十七日的天子!多可笑!”许广汉醉酒大笑,絮絮叨叨的继续道,“霍大将军收拾了上官桀他们。我没有找到麻绳,就从宦者丞被罚去掖庭做鬼薪,后来又升了暴室啬夫。然后我就遇到了你,我的女婿。那时候你还那么小,住在掖庭宿舍里,跟随东海澓中翁学习诗三百。”
刘病已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岳父,你会恨吗?孝武帝和大将军,他们让你受宫刑、做鬼薪,你恨吗?”
“今天之前,我会恨。”许广汉遍寻不着耳杯,索性放弃了,“现在不会了。”
刘病已将自己的耳杯也收了起来,揽着岳父的胳膊,把他扶到榻上。许平君在父亲酒疯之前就被丈夫安排抱了儿子下去,如今床榻很是宽敞,刘病已在上面早就铺好了柔软的被褥。
许广汉握着他的手:“病已,我曾经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我没有拿错别人的马鞍,如今会是什么样?”
刘病已不再说话,轻轻帮他掖好被角。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我会死的!死很惨!“许广汉又道,“菜市口,在杀人!杀的是昌邑旧臣,两百多个,全都是我曾经做过的昌邑王郎!一地血淋淋啊!
原来,受宫刑、罚鬼薪、做暴室啬夫,这些都不算苦难,而是在帮我避祸!拿错马鞍,不是我的不幸,原来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我继续做郎官,一定会在昌邑哀王死后追随刘贺,也一定会成为今日菜市口屠刀下那两百多条亡魂之一。可现在,我还能跟你喝酒,还能抱抱我的小外孙奭儿,何恨之有?”
许广汉大笑起来,刘病已没有笑:“原是我浅薄,岳父豁达,你说得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许广汉倒了下去,门口却传来熙攘的声响。
“你们找谁?”许平君抱着儿子,看到自家门口乌压压站了一堆人,疑惑道。
未几,一位精神矍铄的青年站了出来,身着曲裾深衣、腰佩绶带,道:“在下宗正刘德,特来尚冠里接皇曾孙的。”
许平君问道:“你们找他做什么?”
刘德含笑道:“大将军霍光特派我等来接皇曾孙入未央宫去的!”
“平君,出什么事了?”刘病已服侍许广汉睡下,出门伸了个懒腰,却被门口的景象给镇住了。
尚冠里小夫妻的门前停了一整队车马,车饰华美,乾猎轻车为主,后还有两辆从车,皆是双马驾辕,装饰奢华。
车前车后侍从足有百人,将大门外的道路都堵了个水泄不通。
刘病已皱眉,望向刘德:“刘宗正?”
他在宗室们公卿朝会的时候曾见过他。
刘德见正主出来眉开眼笑:“皇曾孙别来无恙啊。”
“次卿。”许平君轻轻拽刘病已的衣袖,“他说要接你进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