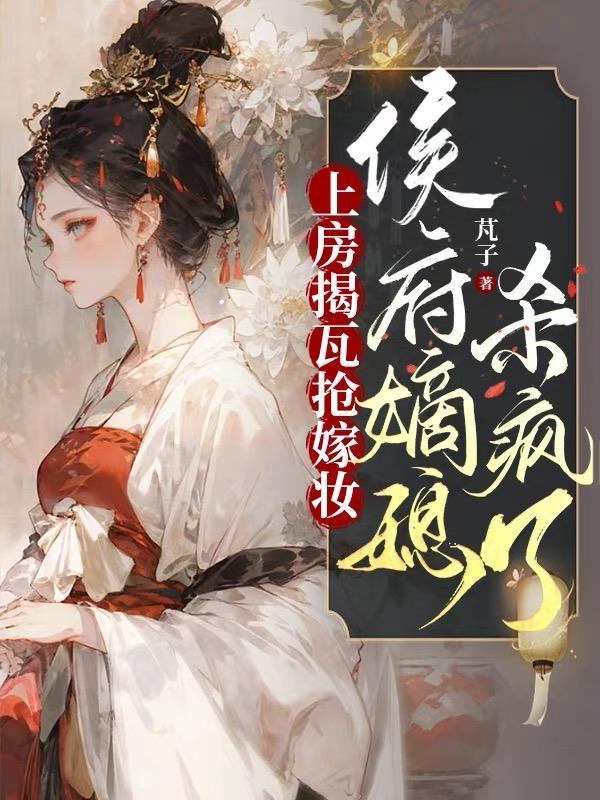UPU小说网>重生后嫁给病弱王爷 月影影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随着萧玦转身,沈姝终于能看见他的整张正脸,一看之下,心尖一颤。
传闻大胤的靖王容貌卓绝,而比他卓绝容貌更着名的,是他冷酷嗜血、杀人如麻的性情。只是沈姝鲜少看见萧玦的血腥模样,毕竟往日萧玦过来,莫不是异常干净,身上带着沐浴焚香后的气息。
然而此时的萧玦太不一样,身上仍穿着黑红间色的四爪金龙纹朝服,袖口有褐色的茶渍,白皙的额头则有一道伤,不知被什么锐利的物什割破,流出殷红的血。
那血划过他的剑眉与长睫,落在脸颊上,又被手指抹开——这样的血迹,配上萧玦苍白的肤色、冷漠的眼神,一时令他有些妖异——倒像了那传闻里令人胆寒的杀神。
沈姝并不害怕,反倒有些担心,不由问道,“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么?”
萧玦听不见她的声音,神情冷寂地朝她走来。沈姝注意到,他的左腿有些僵硬,这使得他的姿势有失协调,近乎一瘸一拐,但他仍将脊背挺得笔直。
难怪他今日走得那般缓慢。沈姝担忧,问道,“你的病又重了些么?”
依旧得不到回答。
这人,总不知道爱惜身体。沈姝幽怨,看萧玦在棺木边站定,低头凝视着她。
沈姝知道此刻的自己是何模样——躺在名贵非常的金丝楠木大棺中,身穿火红的嫁衣,再年轻,再貌美,再如何用冰块冷藏,也藏不住满脸的腐败之气。
一定很难看。
然而萧玦仿似擦觉不到她的难看,只那样寂静而专注地看着她,眼眸里仿佛浸满了多少岁月亦无法承载的沉重心事,让沈姝望之心酸。
“殿下?”沈姝再度担忧地出声,却只是徒劳。
萧玦默然望了沈姝许久,忽然缓缓伸手,一寸寸朝沈姝靠近。他的手指沾着他的血迹,轻轻按上沈姝的唇,而后用了些力。
萧玦第一次触碰她,是将她的尸身从冰冷的溪水里捞出来。
彼时他浑身浴血,仿佛从地府爬出的恶鬼,随意地将两个血淋淋的头颅——其中一个甚至是他的妹妹——扔到一边,差点将簪子上的沈姝吓得魂飞魄散。而后他不顾冬日溪水的刺骨冰寒,跄踉着扑进水中,给了她一个充满血腥与冰雪味道的拥抱。
那时沈姝并不认识他,被他连串称得上惊世骇俗的举动所震,连声骂他是疯子。
疯子给她敛尸骨,设灵堂,让她的仇人一一跪在她的灵前,看他们痛哭流涕,而后冷酷地一刀一个。
其实沈姝的仇人并没有那么多,只是萧玦牵连太广不管不顾。灵堂里血流成河,看得沈姝从惊惧逐渐变得麻木。
那是沈姝见过,萧玦最疯的一次。后来萧玦恢复平静,却又仿佛更疯了。他不给沈姝下葬,而是将她安置在了他卧房下的密室,奢侈地用无数冰块冷藏,某次又忽然心血来潮,给她换上了嫁衣。
他常来看她,似是怕身上血腥之气唐突了她,每每沐浴更衣;有时笑有时哭,有时一言不发,有时又温柔地抚摸她冰冷的手指和脸颊。
初初他触碰她时,她气得骂他是混账、登徒子,没有一点用处,后来便骂不动,由着他来了。
只是嘴唇到底是敏感的地方,沈姝觉得,如果自己还有实体,此刻脸颊一定会变得通红,半是气的,半是羞的。
萧玦按上她的唇,沿着唇瓣细细描摹,好似在用自己的血给她涂抹口脂。沈姝感觉不到他手指的温度,只觉得兴许和自己一样冰冷。
萧玦描摹完她的唇瓣,又揉着她的唇角,一眨不t眨盯着她,蓦地轻轻一笑。
他笑得温柔又悲凉,让沈姝心中酸涩。她听见他轻道,“笑一笑啊,娉娉。”
娉娉是她的小名。多少次,他在这暗无天日的密室,温柔地唤她娉娉,如此隐蔽,如此亲昵。而她想破脑袋,也想不出高高在上的靖王,怎么会认识她,还如此熟稔。
可死者已矣,她再也找不出答案了。
她死了啊,死人怎么会笑呢?沈姝想着,心中酸楚。
如果她不是一支簪子,如果她还活着,她会笑给他看的,也许还会大着胆子抱他一下聊表安慰。
可惜没有如果。她已经死了。
萧玦似是也清楚这一点,没再强求她,收回手指,又定定凝望了她许久,而后转身。
沈姝以为他要离开,正要轻声道别,不料萧玦却是走到正对面的墙边,将墙壁上又一盏兽头灯盏点燃。
七盏兽头大灯全被点燃,将密室照得有如白昼,沈姝心头的狐疑也到了顶点。
火油熊熊燃烧,将密室四角的冰块加速融化,烟与雾缠绕在一起,透露出浓浓的不详。
沈姝感觉自己声音都紧促了些,一眨不眨“盯”着萧玦,“殿下,殿下,您到底怎么了?”
萧玦一无所觉,取下第八盏兽灯的灯盏,又回身走向沈姝,脸上是诡异的冷静。沈姝却隐约觉得,他好像又到了不管不顾的疯狂时刻。
萧玦走近棺木,抬手,举盏,下一刻手腕轻翻,将灯盏内的火油尽数倒入了棺木。
他要烧了她。意识到这一点,沈姝并不如何害怕,反倒有些放松——早该如此了。他早该想开,放她离去。
然而她没有料到,倒完火油之后,萧玦随意地将灯盏丢到一边,而后长腿一迈,竟是也跨入了棺木中。
这是要做什么?沈姝心脏提到顶点,焦急地看着萧玦的衣摆也沾上了火油。
这是要做什么?沾上火油他也容易烧起来啊!沈姝心急如焚,恨不得生出双手,将他推出棺木,推出密室,推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