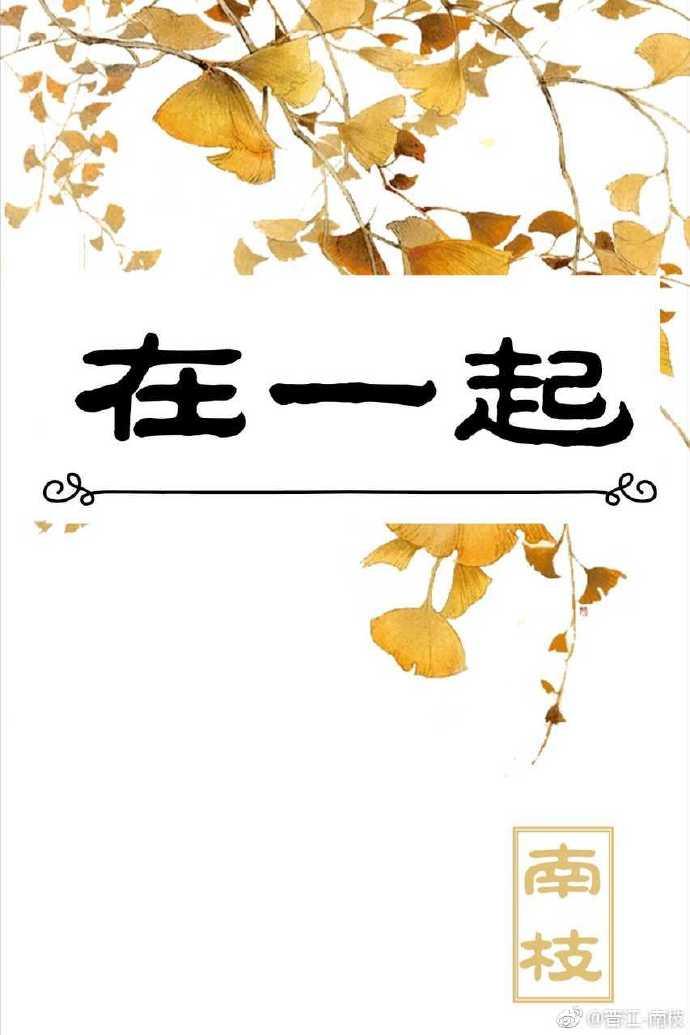UPU小说网>锁娇莺 梅燃 > 第57章 我不是你想的那人(第1页)
第57章 我不是你想的那人(第1页)
白舒童也不知道顾承璟对哪处风景感兴趣,于是车开到了哪里,她就介绍哪里。
这是做向导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不用外语。国语温温也亲切,带着点南方人特有的小口音,听起来软,给夜加了柔意。
前头的司机没有回过头,按着吩咐一圈圈地绕外滩,车开得很慢,旁边的黄包车夫经过都不由得转头看一眼里头悠闲的公子小姐。
好奇,怎么四轮开得比他两条腿的还慢。
是在做什么。
仔细看车内,洋车里,公子懒倦随意地靠在车座,手搭在车窗沿,被小姐的一番话吸引了,指缝间的烟忘了动,积了长烟灰,随风而落地。
他话不多,彬彬克制,也有礼,最多是偶尔目光随着她纤薄手指往外看。
“那有两个高尖了望塔的建筑是之前的德国总会,TheClubConcordia。巴洛克建筑风格,曲线形尖顶,建造的时候花了55万银子。后来民国六年,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加入一战协约国,废除中德、中奥条约后就回收了回来。现在空置着……”
“前面是南京路,这附近有绸缎庄,还有许多百货,是逛街的好去处。”
“再往前是苏州河,上海的母亲河,远眺过去,河对岸,一盏盏暗黄的灯光那里,就是高细的暗影那,是闸北区。。。。。。”
“那里停靠的船只都是近期才被安排回来的闸北难民。。。。。。他们。。。。。。”
白舒童哽了下,看了眼远远的影子,昏暗的汽油灯下,船民赤脚站在船头,穿着麻衣,是缝了又缝的。
岸边还有很多就地而席的人。
因为国弱而家破,无处归港的人很多。
她没有再说下去,回头看了眼也没怎么出声的顾承璟。
他一路都听着,没有任何的打断,黑瞳里暗暗如无垠的夜,让人猜不透,见她停了,才抬了鸦羽,不深不浅地看了她一眼。
“不想说这个,就不说。”
白舒童点点头。
相信没有多少中国人能提起那三个月,而不感到壮烈悲恸。
当时战事逐步升级时,广东空军组成了混合机队也到了上海来,顾承璟刚完婚的学长就在这场战事中坠机牺牲。他此次来,不仅是处理婚事,也参加吊唁。
两人眼里有同样的理解,轻也淡,但足够在这个夜里化成绕指柔,产生了某种依偎感。
白舒童也不知道他是知道她在码头才来的,还是偶然碰见她。
轻咬了唇,问,“军官长,你怎么会在上海?”
其实她更想问的是,他为什么会在白公馆。
他那个订了娃娃亲的未婚妻难道是白曼露吗?是那个她所知道的白小姐吗?
也因为这样,在广州城他才处处照顾她吗?
白舒童尽管不被白家接受,心里有怨怪,但是对从未见过面的白曼露,在心里还依旧是姐姐,也就诡异地,此刻她有种不应该和顾承璟在这里单独相处的窘迫感。
他应该是将自己当姐姐了。。。。。。
顾承璟手上的烟已经灭了很久,没有再点,见着她问了话移开了视线,还转了身去看窗外。
她的夹袄羽毛又在线缝里欲出不出,他真的很想帮她拔掉。
于是静静地,伸了手。
也同时回答了她的问题,“来退婚的。”
“和白小姐退婚?”
“嗯。”
“为什么?”
“我的原因。”
白舒童僵了下,感受到肩边有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温度热,是一转头就能触到的。
她没敢动,轻低了下头,脸有点热。
他却还在肩头处左右拍了拍,拍走碎羽,拉扯起线头的时候,扯上了她的发丝,让她忍不住轻啊了声。
这声音怪得。
让两人都想起了同在白公馆会客厅的那晚,春水潮涌的,怎么想都不能算干净,也不能算完全没有心思。
司机抬眼看了眼后视镜,扫了眼后座。
明明两人隔得远,怎么发出这声响。
然后就听见了白舒童说,“你扯到我头发了,在做什么?退个婚,军官长拿我头发撒气啊?”
“我至于拿你撒气。”顾承璟淡笑,手中却是已经来不及,真的扯了她半截的长发丝。
她冷眼低眸看了他手中黑色发丝,抬手拍了,清脆的一声响后,她说,“松手。”
但也因为这一拍,顾承璟又让她痛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