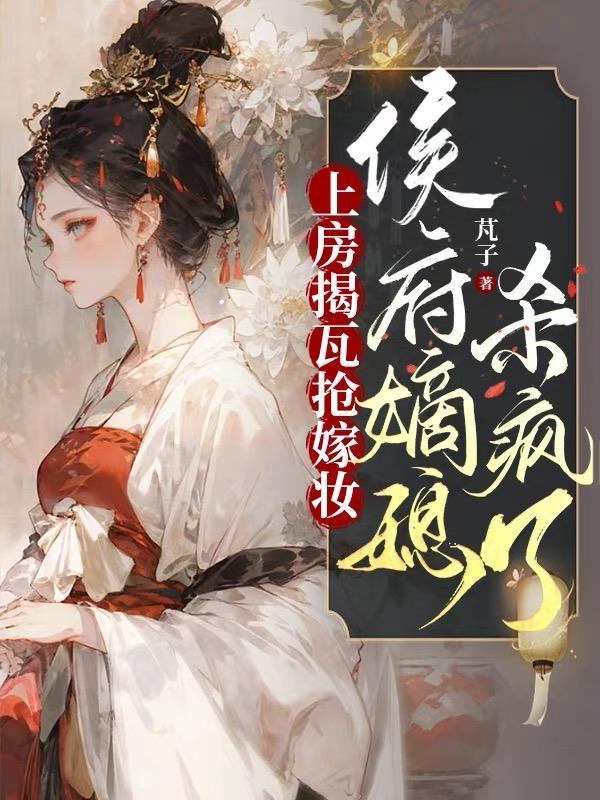UPU小说网>罪与罚英文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虚弱地、坦诚地将自己摆在她跟前。
不是乞求怜悯,只是太难维系全貌,难过得连伪装都不会了。
少年赤诚,心心念念地沉浸在一段感情里,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疯狂无谓,但是唯独接受不了一厢情愿。
他因她烧起一把火,肖洱却毫不留情地一抬手扑灭了。
“肖洱,你不明白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小聂铠灰暗的世界里,她是第一束光。
这世界的光亮很多,可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就算遇见了,那第一个出现的人,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聂铠也不会明白,他对肖洱来说意味着什么。
初次见面,便给她带来数年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维系的家庭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恐慌。
而后种种,他在肖洱的世界里,从来都只有一个名字。
白雅洁的儿子。
是不是聂铠,没有所谓。
肖洱把书包背带从他手里抽出来。
“聂铠,别这么幼稚。你已经成年了。”
他只是难受。
特别特别难受。
他宁可聂秋同再把他打一顿也好呢。
自始至终,他也没有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连改都没有机会。
“好,分手。我不会再找你了,不会起那么早,陪你上学了。也不会随叫随到了。”
最后,他说。
肖洱的身影顿了顿。
“那很好,我也不会再联系你。”
肖洱像是等不及,她一出门,就打开手机,在通讯录里删掉聂铠的名字。
确认删除联系人?
确认。
肖洱回家的时候,沈珺如多看了她好几眼:“怎么了今天?”
不等肖洱回应,一只手已经伸过来按在她额头上:“没发烧啊,怎么脸色这么不好?”
她顺着她的话说:“不太舒服,大概着凉了。”
“晚上不要贪凉,这都入秋了。”沈珺如叹口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道理还要妈妈一再重复吗?”
肖洱摇头。
沈珺如见她实在是没精神,也不再多说什么了,让她去屋里躺着。
“我给你冲杯板蓝根,你作业先不急着写,明天刚好礼拜六,在家多睡会。”
“嗯。”
肖洱带上房门,竟真觉得头重脚轻。
她一头栽在床上,连书包都没摘,睡了过去。
为了今天这一出,她昨天一整晚没有合眼。
那个熟悉的梦,在她身心俱疲的时候,再次入侵。
天地变色,海像有了人性,发着脾气。
巨浪滔天,船只飘摇浮沉。
肖洱好几次差一点吐出来。
她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不在船里。
她就是那条船。
肖洱是被渴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