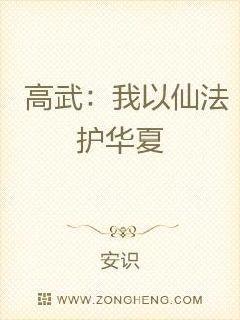UPU小说网>济州四季餐厅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柳时序没想到是这样的事情,他的抵触心理也没那么大了,“是什么生意呢?”
柳仁勇指了指信封,“里面有信息和地址。”
柳时序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他看到一张风格古朴的名片,名片上写着fourseans,济州四季,“他是开酒店的?”
“嗯,这段时间你帮他打理下吧,回来正好拿毕业证书,我在公司已经给你留好位置。”
柳时序心里还是不那么情愿,他从小在纽约长大,朋友都在这儿,习惯了纽约人声鼎沸的欢闹日子,去济州岛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在古代无异于是被流放边疆。况且他这辈子都还没去过济州岛,人生地不熟的,多没劲儿。
但是他知道他是违抗不了爷爷的命令的,更无法拒绝爷爷的请求。
于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他手里捏着那张一个月后飞往济州岛的单程机票,心情复杂地走出公司大门。他仰起头,看见公司的名字和logo在晨光下熠熠发光,大楼的玻璃面折射出璀璨的光晕。
与它比邻的还有无数栋高高低低的摩天大楼,冷酷刚毅地矗立在那里,沉默地见证这个城市男男女女的欲望、野心、梦想,还有心碎。
飞机在上海前往济州岛的高空中剧烈颠簸,客舱里的乘客发出一阵慌乱的骚动,有小孩尖锐地哭叫起来,紧接着广播里传来机长冷静的安抚声,“目前飞机受气流影响产生强烈的颠簸,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不必惊慌,我们会带大家安全着陆。”
迟航刚要沉睡的意识一下子又被唤醒了,他揉了揉眼睛,转头把脸贴近机窗的玻璃,外面是一片茫茫的灰色迷雾,飞机的侧翼若隐若现,在强气流里剧烈地颠簸震颤,像一只穿越黑森林的蝴蝶,脆弱、不堪一击,随时会折翼。
随着头顶的警示灯又一阵急促的嗡鸣,他的心脏被抛起又坠落,失重的感觉让他倍感不适,左眼皮“突突”跳起来,双手不由自主地捏紧座椅。
他闭上眼睛,自嘲一笑,原来自己还是怕死的。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再睁开眼的时候,飞机已经摇摇晃晃地在济州国际机场着陆。
彼此陌生的乘客在经历了刚才那一阵惊慌之后相互露出宽慰安心的微笑,起身拿行李的时候更是多了一份礼节。
迟航的左眼皮还是突突”跳着,他有些疲惫地按着眼皮,跟着出关的人流一路向前。
这时同行的人中间爆发出一阵雀跃的惊呼,“哇,快看!下雪啦!”
航站楼的自动门打开,冷冽冰凉的空气铺面而来,迟航想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便冒着冷意走出了航站楼,他抬头朝前看去,还没来得及欣赏飘扬的雪花,黑框眼镜上已经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模糊了视线。
他近视度数并不高,摘掉眼镜也可以看清天空洋洋洒洒飘落的雪,还有马路正对面的棕榈树间“hellojeju”几个大字。
寒风裹挟着雪花吹到他的脸上,他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很快又退回到航站楼内。
他的目的地在西归浦,位于济州岛的南面,距离机场40-50公里。西归浦离市区有些远,也没有特别出名的景观,很少游客会全程把住宿订在那里。迟航一开始是被民宿韩式古建筑的外观吸引,等他临近出行再细细查了攻略,才发现民宿的地点有点偏,再想退款已经来不及了。
济州岛很小,住哪里都一样,何况他这次有的是时间,每天环岛跑一圈也不是什么问题,他这么想着,便说服了自己。
从机场到西归浦,打车要好几百人民币,迟航舍不得花这笔钱,决定坐公交过去。反正,还是那句话,他有的是时间。
他在绿色的巴士后座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巴士很空,只有几个老人零零散散地坐着,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
和表情呆滞的老人不同,迟航毕竟第一次来济州岛,岛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托着下巴,饶有兴趣地打量窗外掠过去的风景。
一开始是频繁出现的咖啡店和加油站、美式建筑风格的快餐连锁店、家庭便利店、朴素的民居,接着人气越来越少,开始出现大片的田地,这个季节的田地里什么也没有,光秃秃的很荒芜。铅灰色的大海卷起白色的浪花,撞在海边黑色的岩石上,像漫出酒杯的啤酒花,海面上盘旋着无数只乌鸦。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单调,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从轻薄的雪花粒慢慢变得如鹅毛般厚重,密密匝匝地落下来。车上空调的暖气明显不足,寒气从车外漫延进来,迟航冷得哆嗦了一下,他下意识裹紧自己的外套,又看了看表,才只开了一半不到的路程,于是他闭上眼,任由自己迷迷蒙蒙地睡了过去。
“航航,大过年的,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方晓萍听到迟航过年的出行计划,皱起了眉头。
“妈,济州岛很近,坐飞机不到两个小时。”迟航解释道。
“你每次坐飞机,我都提心吊胆的,大过年的就应该安安生生地在家待着,别让我们担心。”方晓萍不满地摇头。
“是啊,航航,听你妈妈的,就待在上海吧。况且过年还要走亲戚,你不在,这怎么办?”迟建州喝着啤酒,也附和方晓萍。
“爸,你们去就行,我跟他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题……”
迟建州重重啧了一声,“就因为你都不走动,跟亲戚才会越来越疏远,你们年轻一辈也该多联系联系,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在屋里。”
迟航不说话了,默默地吃饭,三个人的饭桌又陷入跟往常一样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