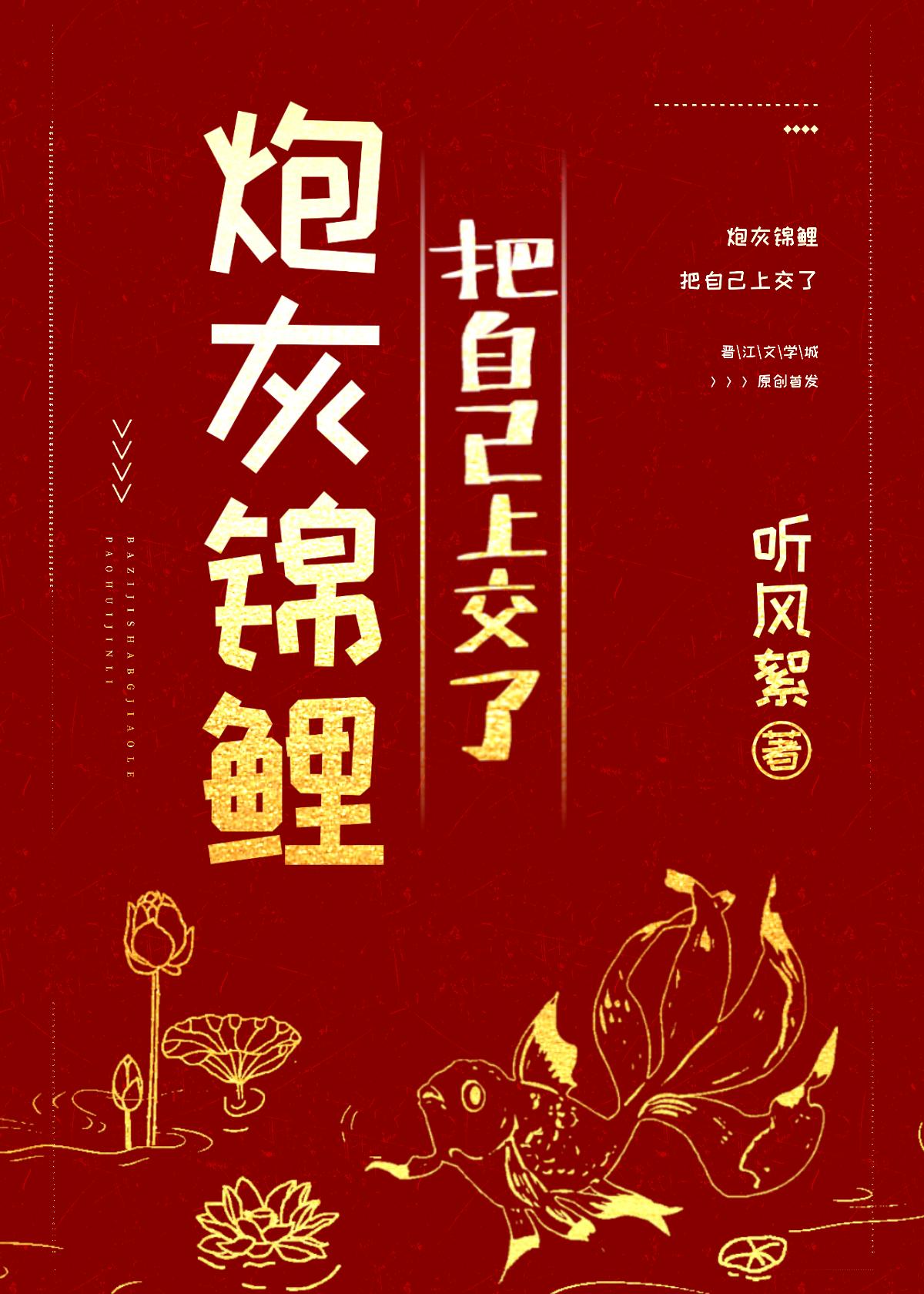UPU小说网>别装全文免费 > 第13章(第2页)
第13章(第2页)
宁柯隔着人流冲他用力挥手:“师父!这儿呢!”
这小孩儿嗓门忒大,陶阮拉高口罩走了过去。
“想死你啦!”宁柯大喇喇地探过身子来抱他,差点碰到陶阮贴了膏药的后颈。
“你脖子咋了?”宁柯问。
“落枕。”
“落枕需要贴膏药吗?”宁柯有些疑惑,但还是对陶阮的话深信不疑。
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他发动车子,“咱今天去吃点儿硬菜……”
所谓硬菜,原来就是海鲜十八式。
五星级的海鲜大酒楼,连帝王蟹都比外面的要大上一圈儿,只不过陶阮兴致缺缺。他昨晚就是被人打晕了带到酒楼,李漆也点了一桌子海鲜,可从头到尾没人动。
“怎么了师父,不合胃口?”宁柯问。他见陶阮一脸不高兴,还以为是不喜欢,当即招手就要喊人撤走。
“别折腾了。”
陶阮制止了他,戴起手套就要开始剥蟹,宁柯直接点了个剥蟹师,动作麻利的比两人吃蟹还要快。
“师父,你真的太瘦了。”
想起方才陶阮戴口罩的模样,三分之二的脸都快看不见,宁柯企图往陶阮碗里添饭,却被陶阮飞了一眼刀。
“吃你的。”
宁柯梗着脖子:“吃着呢,我吃的可多……”
吃完饭,宁柯把他送回幸福家园,陶阮从包里拿出一张光盘,“回去多听几遍。”
宁柯眼冒星星,抱着deo“嗯嗯”两声。
“好了,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陶阮说。
送走宁柯,陶阮手机嗡嗡的开始振动。这次他走的正门,小区门口灯光很亮,屏幕上显示,来电人,陈福寿。
陶阮突然有些耳鸣。
小陶公主
陈福寿是他的继父。
爷爷走后,他毅然决然搬离那个破旧不堪的筒子楼,单方面切断了与陈福寿的联系。起初陈福寿还会想方设法地打探他的联系方式,然后狂轰滥炸似的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每一次陈福寿一找他,除了要钱,还是要钱。
后来几年,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陈福寿发达了,不仅换了房子车子,还搂着情妇到旧街坊面前炫耀,狠狠出了一把风头。
“哟,了不得啦,还有专人车接车送的嘞!”
“还是四个圈儿的车呢……”
陶阮对此并不关心,依旧该吃吃该睡睡,过自己的日子。但他这么想,不代表陈福寿也这么想。发达了的陈福寿坐立难安,一会儿派人来警告他,说自己早把他养大,已经尽了义务了;一会儿又合计着把他户口迁出去,更有甚的,还打起了移民国外的主意。
说来说去,就是怕陶阮找他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