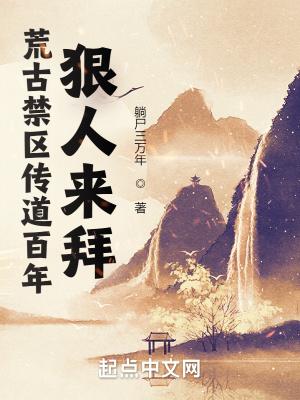UPU小说网>三国风云人物 > 第九十三章 一念之间(第1页)
第九十三章 一念之间(第1页)
年,本是又一个循环,又是一个,本该团圆,却不得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啊,年难过,难过年,年关而已,年关而已,大汉版图之上的百姓们,年年岁岁如蝼蚁,朝朝暮暮不得闲,却依旧饥寒交迫,苟延残喘。
长安,李儒恨吕布恨的牙根都痒痒,就这样恨着恨着,李儒长叹一声:“若是文开(华雄表字)尚在,何止如此啊,”
一声长叹过后,李儒猛然惊醒:汜水之战伊始,本该是吕布前去镇守,但华雄不服吕布,立下军令状,赶赴汜水,结果却一去不回,长眠于地下,而自那时起,吕布以及一干并州旧将便与凉州将领之间隔阂日深,吕布虽莽撞,却并非愚笨之人,怎会不知将董卓已死的消息散布出去的危害,。
李儒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可是,这究竟是哪里出了纰漏呢,为何只有李榷、郭汜率大军前來,而其余凉州将领如樊稠、张济却毫无动静。
“嗨,”李儒一拍大腿,心道:定是那个娘们多日不见岳父,又看我那段日子心神不宁,便派人尾随于我,皆是太师府人,家丁也不会过于注意,害我险些冤枉了奉先。
其实以李儒心智想到这层并不困难,只是因为气量不足,会被一叶蔽目。
“來呀,备马,”李儒并非拿不起,放不下,死要面子的人,既然已经想通了其中梗概,再不迟疑,边向外走,边大声道。
太师府一小厮,陪着谄媚的笑脸道:“郎中令,怎不坐轿,今儿改骑马了,天气寒冷,骑马风大啊……”
李儒不耐烦的摆了摆手打断了那小厮的喋喋不休道:“修要多言,速速将马匹牵來,”
那小厮知趣的不再言语,转身牵马去了。
长安街道之上,不甚宽广的街道之上,李儒打马如飞,肥大的衣服灌了风,衬的他的身躯更加消瘦和有几分佝偻。
执金吾府邸,吕布闷闷不乐,正与高顺对饮。
高顺一如既往的沉稳,坦然道:“温侯心中不快,何不与那李儒当面对质,一解心中之疑,”
吕布一仰脖将一盅酒喝下道:“高顺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可曾觉得委屈,不提李儒,今日只说你我兄弟,不知文远现在如何啊,”
“唉,”高顺深知吕布脾性,便不在多言,“赵风能以上万军士的生命换得文远,足以说明此人眼力非凡,文远大才,顺不及其万一,”
吕布道:“你的意思可是说我不识文远大才,”
高顺爽朗一笑道:“当然不是,将军高义,何尝不是为了成全文远,”
“知我者,高顺也,來,喝酒,痛快,不枉你我兄弟相知一场啊,”吕布说到这里,心情大好。
“报,~~两位将军,李郎中求见,”一个吕府家丁道。
“噢,來了多少人,可是前來兴师问罪,,”吕布拍案而起,杀心已动。
“回将军,只他一人,”
高顺拉住了吕布的胳膊道:“温侯暂熄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且见他一见,看他來意,再做打算如何,”
“不见,”吕布斩钉截铁道。
“奉先为何不见,儒乃是负荆请罪而來,还请将军看在太师面上,与儒一谈,”李儒此时已经出现在了院门口,言辞恳切道,想执金吾府的家丁,谁人敢阻拦李儒,尽管现在传闻董卓已死,可一日不见董卓尸骨,就沒有人敢对李儒无理。
吕布沒想到李儒会闯进來,那自己方才所说之言,岂不是尽入他耳,干咳两声道:“布本想拜访李郎中,却不成想李郎中会亲自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啊,”
高顺道:“顺告辞,”
却不成想,吕布与李儒竟然异口同声道:“不必,”
李儒接着道:“高顺将军乃温侯左膀右臂,不必见外,此事关系重大,当速速拿出一个万全之策啊,”
三人说到这里,携手入内,李儒踮起脚尖,帖服于吕布耳畔道:“将军当令人戒严,以免重蹈覆辙,”
李儒这一句话,令吕布如梦初醒:对啊,俺只想着太师府戒备森严,却不曾想太师府人数众多,难免鱼龙混杂,想李榷、郭汜胆敢带兵进长安,定是其在太师府中藏有细作……唉,真,真,真……
想到这里,吕布面红耳赤,口中道:“传令下去,此屋百步之内,不得出现任何人,如有违令者,杀无赦,”
那小厮立于门外拱手道:“将军尽管放心,”便转身径自去了。
顷刻间,这小院百步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刀出鞘,弓上弦,别说是人,就连一只蚂蚱也蹦跶不进去。
李儒轻轻推开窗户,向外观瞧,赞道:“执金吾府较之太师府,胜强百倍,儒心安也,不知这些军士是哪位将军带出來的,”
吕布呵呵一笑道:“文正,这些皆是某的并州旧部,也都是高顺一手带出來的,”
高顺虽被李儒赞赏,脸上却无半点骄纵之色,好似与他无关,心如止水,朗声道:“李郎中 谬赞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之前误会,想必奉先也不会与儒计较了,”
“惭愧,惭愧,只是不知是何人所为,,布断要将其碎尸万段,”
李儒先是点点头,后摇摇头,一脸轻松道:“无妨,既然消息泄露,何不将计就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