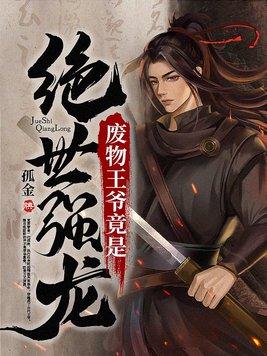UPU小说网>小夫人又美又甜全文阅读 > 第22节(第2页)
第22节(第2页)
打开来,从中拿出一根婴儿手掌大小的玉牌吊坠,一扬手,挂在了她脖子上。
“这什么呀?”
阮阮低头拿起来接着烛火瞧,见上头有小字,便念出声来:“旭丰年甲子日卯时一刻,霍氏第二十三代子孙,修,字昼白。”
“啊!”她忽地轻呼一声,睁大眼睛看他,“这是你的庚帖!”
权贵人家就是非同一般,庚帖居然是玉雕刻的,想当初她偷偷跑进来翻了那么久,还打开这盒子看了眼,却都没有发现……
霍修嗯了声,“收好,若是像那簪子一般随意丢,我定要罚你的。”
阮阮“唔一声,“这还算你有些诚意。”
拿了信物,她一颗心定下不少,郑重应下了,“庚帖都在我手上,你来年可不能耍赖了。”
他也说“嗯”,望着她面上心满意足,轻笑了声。
阮阮手掌覆在玉牌上呼出一口气,兀自嘀咕,“回头我找人瞧瞧咱俩八字合不合,若是有问题,也好早发现早化解。”
这厢话音方落,便直觉他凌厉一道目光立时直射过来,她吐了吐舌头,“肯定合的,咱们俩是天作之合!”
瞧她那样子,拿着玉牌翻来覆去地看,像是个孩子得了心仪的把戏,爱不释手。
霍修收回目光,垂眸笑了笑,背着手往外间去了,唤她,“快出来,天还没亮,再陪我躺会儿。”
阮阮答应着,过了半会儿才出去。
她双手藏在身后有些鬼鬼祟祟的,临到床边忽地拉起他的一只手,拇指指腹上蹭一蹭,随后吧唧,印在了一张纸上。
“还是要有个凭证我才安心。”
看他皱眉,阮阮忙又辩解了句,“主要是你往后若有了新欢,我能送凭证去恶心你们,至于玉牌,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砸碎了也不会给出去称你们的意。”
霍修从前没发现,她骨子里还有些睚眦必报的气性儿呢。
“随你,喜欢收就收着吧!”他冲她招手,“来,过来让我再抱会儿。”
这一抱,又燎起冲天烈火,轰轰烈烈烧起来,几乎要教人灼晕过去。
翌日太阳照进床帐中,阮阮才朦朦胧胧睁开眼,缓过神儿,倒不似从前那样着急。
她现在已经不用担惊受怕了,甚至在考虑找个合适的时机将事情告诉爹娘,免得他们到时候毫无准备,再吓着了。
慢悠悠伸个懒腰,慢悠悠支起身子在房间中找了找霍修的身影,没找着,后来才听婢女说:“大人卯时末已出门去了,留下话,说傍晚去接小姐一同用晚膳。”
阮阮嗯了声,收拾完了出偏门,却见画春正靠在凤鸾春恩车旁边儿,等得百无聊赖。
听见脚步声,画春抬起头,瞧着她便忙迎上来,“小姐怎的才出来,差点儿担心死奴婢了,下回可不能再误时辰,否则老爷夫人那儿,奴婢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说起这个,阮阮拍拍她的手,信心十足说没事,“放心,很快你就再也不用和我一道担惊受怕了。”
画春狐疑:“这话怎么说?”
阮阮冲她神秘一笑,先不言语,拉着人上了马车,才献宝似得从衣领里掏出玉牌给她瞧了眼。
“他都答应了,来年这时候就要明媒正娶我呢。”
“来年?!”
画春对于阮阮面上的笃定只觉十分不可思议,“小姐莫不是又被那狗官蒙骗了吧?若是真心求娶,为什么非要等到来年?”
其实搁谁听了都是这么个想法,可阮阮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就是觉得霍修不是那种使阴招坑骗姑娘感情的小人,虽然,他会明目张胆地趁火打劫……
“是他亲口说的,而且也把庚帖交给我了,改日你陪我上慈云寺去找大师瞧瞧八字。”
画春觉得她有些太乐观单纯了,对上狗官那样的人,搞不好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银子呢。
但眼下无凭无据也不好迎头打击人,只好警醒了句:“总之小姐记住,夜长梦多,梦多易生变,既然小姐铁了心想做霍夫人,那有机会还是教他尽快上门提亲吧!”
主仆二人这厢正说着话,却听周围街道上似乎有人群拥堵,马车也渐渐缓慢下来。
仔细听,有人说:“前头搭台子的那不是卫家那二郎嘛,他这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他要当众向阮小姐求亲?”
“真不要脸,咱们鄞州的第一美人凭什么就便宜了那外来的小子?”
“就是,走去看看,咱们这么多人,定要给他个下马威!”
………
呀!
阮阮听着才想起来,卫霁昨日是说要在闹市区搭台子当众澄清呢!
她忙敲车门示意侍卫停车,找了个偏僻的地方下来,便教人回去了,自己带着帷帽去了人群聚集处。
四方的高台左侧一面打鼓敲得震天响,中央摆一把宽大的太师椅,卫霁泰然端坐其上,手中端一盏茶,只等着四下瞧热闹的人群围过来。
看着差不多了,他起身,将手中茶盏交于小厮,一旁鼓声见状立时停了下来。
卫霁冲下头的人群拱了拱手,轻咳一声,朗声道:“诸位稍安勿躁,今日摆出这阵势,是要请在场各位做个见证。”
“我卫霁在此,郑重向阮乐安道歉,城中流传她是我未婚妻子之流言是我前日一时口误,迄今为止还并未真的有这事,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