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U小说网>基督教诗歌欢迎回家 > 第13节(第1页)
第13节(第1页)
那边时为却已经放下拖把,对高师傅说:“你下班吧,我来。”
丛欣眼见着高师傅脸上一闪即逝的微表情,那意思仿佛是,这马屁也要抢?
但时为当然无所谓别人怎么想,只是背身在水槽那里洗手,然后去开冰箱,拆了一份牛肉,切两只彩椒,又问高师傅有没有米酒。
“我习惯用米酒。”他说。
丛欣觉得高师傅大概在心里翻了个白眼,但还是在架子上找出来给他。
只有她知道,这话是冲她来的。
她两三岁的时候挑食挑到几乎绝食的地步。当时人小,不太会表达,只会哭诉猪肉太猪,牛肉太牛,鸡肉太鸡,鱼肉太鱼。但还有些菜明明一点荤腥都没有,她闻到照样打恶心。
张茂燕快给她折腾疯了,怕她饿死,带她去看医生,得到的医嘱是再饿两顿。也就朱师傅愿意相信小孩子的嗅觉和味觉特别敏感,每天做实验似地给她找原因。
最后发现是因为黄酒。
那时候江南一带都拿散装加饭或者花雕当料酒,只要菜里搁了,她就不吃,于是从此江亚饭店职工楼四楼最西面那一间的厨房里做菜全部改成用米酒。
这怪毛病后来当然好了,也不用什么药,只需长大,便可以根治一切矫情。他现在又提起来,大约是在谴责她忘恩负义。
小高师傅已经打卡离开,食堂没有其他人。她在餐台边坐下,看着他把肉切片,下料拌匀,处理了配菜,又去下面。
灯光直白,不锈钢冷硬,与楼上的酒店截然不同,像是被一道沉厚丝绒隔开的台前幕后,但此刻水汽蒸腾,让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也带上了一种氛围感。
“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终于问。
“找你干嘛?”他反问。
她无法回答,自己确实早已经放弃了替他出头的冲动,也没办法为他做什么。但这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她想说。
而他已开火热锅,将肉片微煎一煎再开始翻炒,很快出锅盖到面上,变成一份小炒牛肉面,放在她面前。
她没吃晚饭,本以为不饿,直到食物入口,抚慰了她整个人。她就坐在那里吃,把那些尚不确定的保证一并咽下去了。
他收拾了刚才用的刀具砧板,找出柠檬酸,开始刷洗面前的不锈钢台面。
她看不过去,说:“你不用做这些,十二点之后有夜班保洁来打扫的。”
他没抬头,继续刷灶台,说:“那做厨师还有什么乐趣?”
她反问:“你做厨师的乐趣就是打扫卫生?”
他倒是笑了,轻轻的一声,说:“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你说的对,这确实是个好机会,这才第二天,就已经有人来给我offer了。”
她不吃了,看着他,不知道这算是真话还是嘲讽。
他也停下手上的动作,看着她问:“你说我应该去还是不去?”
她没说话,食物在一边腮帮鼓出一个包。
但他似乎又一次误会了她,说:“你放心,说了做一年就是一年。头衔还是CDC,薪水照发,别说做员工餐了,让我去夜排档也不是不行。”
她以为他说气话,把面条咽下去,努力给他解释,说:“你别这么想,这个安排只是暂时的,而且还有行政酒廊,要是把那里的问题……”
他又笑了,打断她说:“丛欣你看不上员工餐吗?你小时候这儿吃饭吃的少了?”
丛欣噎住,说话癫到一定程度,让人没法接。
他回头,指给她看后面一扇红色的门,忽然问:“是那里吗?”
看标识是个工作间,但她立刻明白他在问什么,是那扇门后面吗?
100年的老酒店,曾经历三次大修。2007年那次是最彻底的,很多地方都变了。但也许,只是也许,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还有那么一扇门一个房间,保留着它原来的样子。
里面铺上简易塑料地板,放上一些玩具和图画书,便成了职工子弟幼儿班。当时总共二十几个孩子,每天挤在一起玩,一起学儿歌,一起做操,一起午睡,中午去同在地下室的员工食堂吃饭。
哪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也算是硬件条件比较差的幼儿园了,因为压根没有“园”。却也有它特别的长处,比如这里的小朋友总能吃到中餐厨房煎的带鱼尾巴,西餐厨房炸的薯条角角,面包房多下来的蛋糕边边。
也是因为那个地方,当她第一次看到麦兜电影里的春田花花幼儿园,莫名泪流满面。她就是这样的人,曾被交往过的男人批评冷漠又自我,有时候却会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小事落泪。比如此刻。
他没再说话,隔着餐台递给她纸巾。
她接过去,擦掉眼泪,低头默默把面吃完。他也已经刷完灶台,从蒸箱里把当天的夜宵拿出来。
“没事早点回去吧。”他对她说。
她回:“你也是,明天开始上五点半的早班了。”
“你怎么走?”他问。
“你怎么走?”她也问。
“自行车。”他回答。
她抹抹嘴站起来,说:“那一起吧。”
他说:“你还是叫辆车吧,每天跑上跑下两万多三万步的,半夜别再折腾了。”
她略无语,说:“你有功夫看我的微信步数,没时间回我信息?”
两人忽然笑了,感觉到一种互相伤害的幽默。
于是便一起下班,各自换了衣服,从员工通道出去,来到酒店后门的小马路上,各自扫了辆共享单车,一起往家骑。
那是个晴朗的初夏的夜晚,月朗星稀,海上的风吹着大团大团的云翻滚前行,似在半透明的黑色天幕上演一出风卷云涌的影戏。
时为骑在后面,看着丛欣的背影。这一天的变故起初确实像是一种折辱,但不确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换了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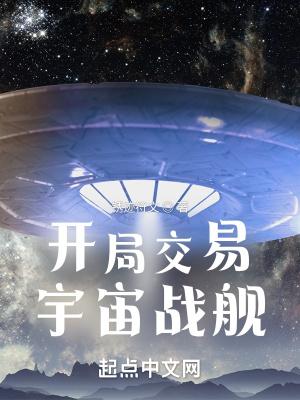
![职业反派[快穿]](/img/1861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