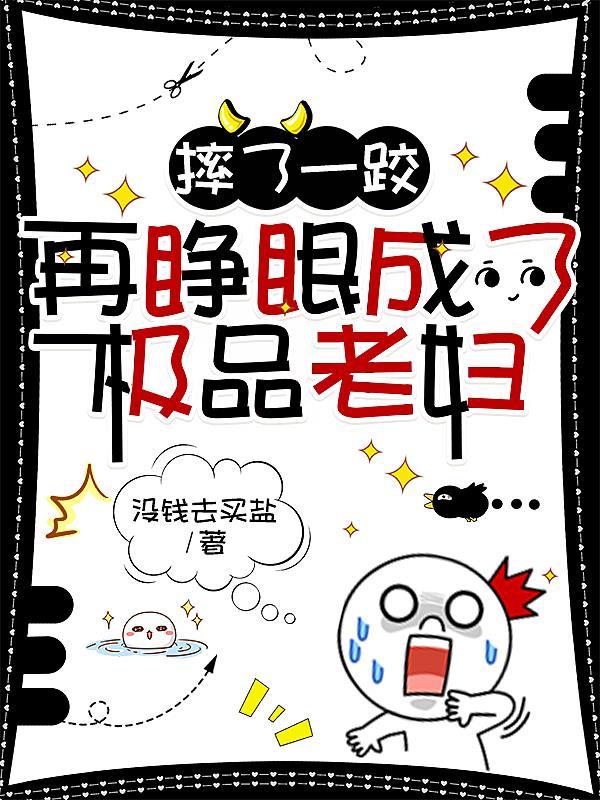UPU小说网>那个小哑巴txt > 54 第54章(第1页)
54 第54章(第1页)
林知言一度以为,“爱”这个词永远不会出现在霍述身上。
哪怕当初和霍述分手时,她心痛得无法言喻,也没有追问过霍述诸如“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一星半点的爱意”这种庸俗的问题。
因为她知道,即便她那时刨根问底似的想要得到一点安慰,霍述也只会昂着高傲的头颅,温柔而又残忍地告诉她:“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住院的那几天,好几次她半夜醒来,看着霍述一个人坐在病房里处理公务,也不是没有揣摩过他的心理。但她始终不敢不往深层想,因为霍述亲口说过,他不需要、也不懂感情。
如果有一天,霍述幡然醒悟,原来他对她的执念根本就不是爱,然后潇洒抽身,林知言该怎么办?如果她永远无法拥有一份平等、明确的感情,她又该怎么办?
总不可能再来一次火灾意外,再逃上三、四年吧。
“还说不是、来做说客,这些话,我要怎么接?”
林知言哑然失笑,和骆一鸣交谈,连手语都不能打,只能逼着自己组装词汇,一开口就暴露了情绪,“他表现出来的,和你说的,完全是两个人。”
骆一鸣说:“那不然呢?你指望他负荆请罪、指天发誓,再痛哭流涕地请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他是霍述啊,你我都清楚,他不可能这样做。”
林知言自顾自颔首:“他是霍述,所以不可能请罪。他是霍述,所以我只能、自己想通一切?”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你即使讨厌他,也不要讨厌错了地方……嗐!完菜,总感觉越描越黑了。”
骆一鸣挫败地挠挠头,“其实你早就看明白了吧?你这么聪明,不会不懂他的意思。你只是太怕受到伤害了,毕竟当年那事儿,的确是他不厚道。我作为他表弟,情感上难免会偏向于他,可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一句也没骗你。”
林知言提了提唇角,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不为难你。谢谢你愿意告诉我这些,但是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楚。”
她看了眼时间,已经快到饭点了,自己好歹是客人,长时间躲着不见人未免有些失礼。
她不在乎霍述怎么想,但她不想让霍家觉得她是个没教养的人。
起身要走,骆一鸣却着急忙慌叫住她。
“林知言,拜托你件事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能不能别告诉述哥啊?他最反感别人议论他的私事,他会杀了我的!”
林知言转身,好奇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骆一鸣瘪瘪嘴,小声说:“你和凌妃的麻烦,毕竟是我惹出来的,你就当我是在赎罪吧!以后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和凌妃还有可能在一起的话,你能帮我说两句好话。”
不愧是商人之子,这么早就想好怎么投资了。
林知言笑了:“那也要,你有好话让我说才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我爸一直想让我继承家业,总之先从家里独立出来,跟着述哥干吧。我能拿出来和家里抗衡的,也只有这么点筹码。”
骆一鸣忧心忡忡地叹了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之前还有点犹豫,今天倒是实实在在被述哥给刺激到了。五年前他连霍家本宅的门槛都进不去,五年后就已经能站在老爷子面前发号施令了,我再孬,五年后也该有一番光景吧。”
他能有这个觉悟,总归是件好事。
林知言不置可否,温声说:“我知道了,祝你成功。”
一番掏心窝子的谈话结束,两人各怀心事,都有些戚戚焉。
“我走了。”林知言说。
“啊?哦,好。”
骆一鸣挥挥手,“记得我刚嘱咐你的话!千万别卖我啊!”
林知言拧开书房的门出来,继而一愣。
霍述一边打电话一边从走廊外进来,眉头蹙得很紧,似乎在催促什么。乍一见到想找的人就在书房,也是顿了一顿。
仅一秒,他恢复镇定,挂断电话。
他缓步向前,有意无意扫视书房内,见到胡乱拿起书本挡脸的骆一鸣,眸子便危险地半眯起来。
林知言此刻已然冷静下来,关上书房的门。
霍述的视线受阻,盯着那扇沉重的实木门良久,方回正视线,松弛地倚站在墙根处看她,目光有种望不见底的深沉。
霍述永远不会逃避,哪怕明知等待他的是最坏的裁决,他只会像现在一样,平静地直视她的眼睛。
“怎么去书房了?”
他率先开口,声音听不出半点负面情绪,尽管他们十分钟前还在为回霍宅的事争执。
林知言回答:“看书。”
当然是谎话,她答应过骆一鸣不出卖他的。
聪明如霍述,却没顾得上揪住她声音里的那点心虚,只是有些诧异的微微睁大眼眸。
而后他很轻地笑了起来,略微低着头,笑得双肩都在抖动。
他笑起来很好看,林知言静静地看着,有些摸不着头脑:“笑什么?”
“我以为,幺幺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霍述收敛了笑,眉梢仍残留着意气风发的轻快,“毕竟我刚刚交了一份零分答卷。我正头疼,这次要怎么挽回形象呢。”
不可否认,骆一鸣那番话还是有些作用的。
譬如林知言此刻见到霍述神采飞扬的模样,就会忍不住幻想三年前的那个春节,他浑身是血地躺在担架上找人的样子。
林知言喉间微涩,轻声说:“很简单,你告诉我、为什么突然带我来霍宅。为什么明知道、我会生气,你还要这么做?”
“是骆一鸣找你谈话了吧。”
霍述了然的样子,向前说,“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