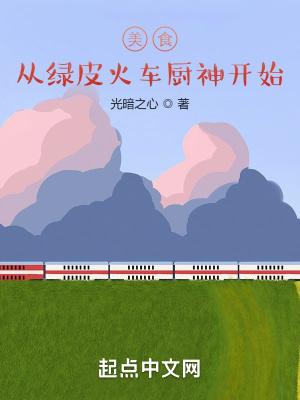UPU小说网>哭坟王是什么意思 > 第十一章 夜游长街(第2页)
第十一章 夜游长街(第2页)
“姑娘能吃爱笑,是个有福之人。”
喜愿心里高兴,应着,“借您吉言。”
“几位是外地来的吧。别的我不敢夸口,就单说这肉饼,整个长宁街,就没有人比我做得更好吃的。就是再往前推个几十年,那也是不曾有的,那时啊长宁街还叫玄忠街,我年轻时就做饼,一辈子都在做饼呦……”
沈植问道:“玄忠街?那为何改为长宁街了?”
“玄忠街是玄景帝在位时的事了。后来先皇登基,那年奉朝各处风调雨顺,恰逢长公主出生,据说因为是先皇第一个孩子,便十分疼爱,视为祥兆,赐长公主名为长宁,寓意奉朝长宁久安,这条街便一同改名为长宁街。”
“长公主便是前段时间薨逝的那位吗?”
老者明显有些忌讳,小声嗤道:“自然是那位。奉朝哪里还有第二个如此受宠的长公主啊。”
说完这话,他不敢再多言语,又去做饼去了。
沈植怕喜愿和风不鸣不解老者的言外之意,解释道:“你们身在江湖,大约不知这位长公主。她虽是女子,却铁血手腕,自她摄政以来,朝堂血流成河,顺者昌,逆者亡。民间有歌谣唱‘奉朝皇,女帝猖。乱世起,皆彷徨’,唱的便是这位想要称女帝的摄政长公主。”
喜愿自顾自地埋头吃饼,手不禁摸上头顶的面具,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半边脸。
而风不鸣难得听得认真,问道:“那她为何死了?”
沈植折扇轻摇,眉眼弯弯,“江湖传言,她启用暗潮阁暗杀朝臣,又在排除异己后卸磨杀驴。暗潮阁的幸存弟子为报血仇,埋伏在围场数日,终将其杀害。当然,这只是江湖传言,风兄听听便罢,当不得真。”
风不鸣敛下眉眼,淡淡地说:“既有传言,想来并非是空穴来风。”
这话说得风轻云淡,事不关己,可那捏住杯子的左手却青筋暴起。
喜愿在一旁咔咔啃饼,难得没有插话。
沈植看向她,问道:“喜愿姑娘如何看?”
喜愿假笑,“未知全貌,不予置评。况且,这人死都死了,到底如何,也不得而知了。哎呀,我吃饱了,我们去别处看看吧。”
她站起身,揉揉肚子,笑得明媚,“也不知有没有卖糖葫芦的,解解腻。”
就这样,三个人从长街的头,一路吃到了长街的尾。
起初,喜愿买一份,风不鸣和沈植也会跟着买一份。
后来两人吃饱了,空出的手拿着的全都是喜愿的吃食。
一直走到渠江池,再也逛无可逛。
喜愿抬手一指,指着湖面的画舫说道:“听闻夜船上的酒不错,我们去尝尝吧。”
沈植压根不肉疼兜里的钱,好脾气地跟着上了船。
风不鸣走在最后,望着平静的湖面思索片刻,才跟了上去。
大的画舫都提前被人订走了,上面灯火通明,歌舞丝竹。
喜愿上的这只船很小,但是坐他们三人是够了的。
他们就听着旁边画舫里传来的歌声乐声,抬头赏天上的月,低头赏湖上的影,手里举着酒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突然,风不鸣的右耳微动,余光凌厉地射向船旁叠起涟漪的湖面。
同时,他右手捏着的酒杯瞬间被掷出,砸向水中突然钻出的黑影上。
只见莹白的月光下刀光泛着冷白,劈在酒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