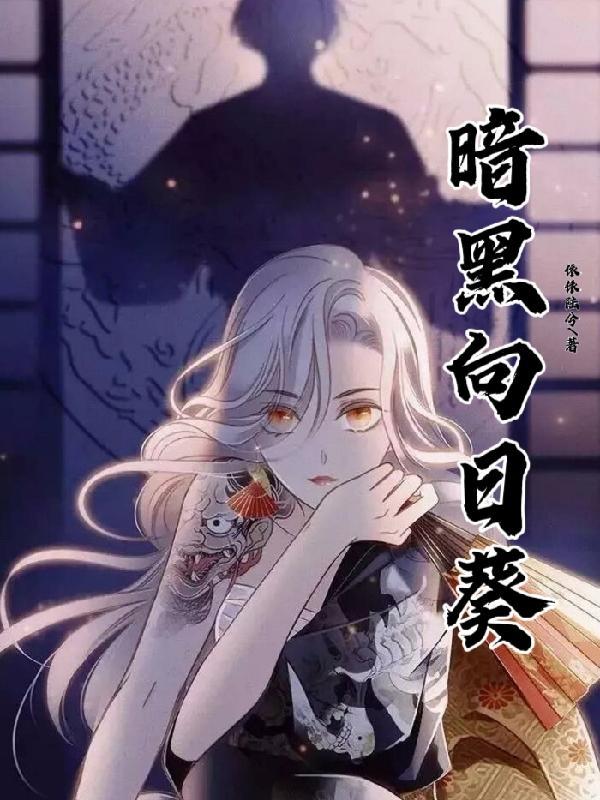UPU小说网>女扮男装入官场 > 第4章 充盈后宫(第1页)
第4章 充盈后宫(第1页)
知音磕磕绊绊问:“大人……您还活着啊?”
时蕴瞪她一眼,兀自坐下,继续啃着桃,看向还瑟缩在一起的几人,“别看了,好端端活着呢,快去做饭来,我都快饿死了。”
几人这才如梦初醒,一窝蜂的出前堂。
知音连忙凑上来,“大人,您怎么回来的?陛下没追究您女扮……”
时蕴捂住了她嘴,比了个嘘,“别叫唤了,他没发现,虚惊一场。”
知音:“您这么久不回来,我还以为您直接拖去午门斩首示众了。”
时蕴瞪她一眼,“就不会盼着点我好。”
她瞧着知音手指绞动衣角模样,心里猛然生出不详预感,“你除了给他们发例钱,要他们走人,还做甚了?”
知音抬眸小心瞧了眼她眼神,手指绞得更厉害了,“这不您说给山长传信要他跑路吗?信……已经送出去了。”
她犹豫了一下,竖起两手指,“两时辰前,飞鸽传书,应该已经出京都了。”
“……”时蕴想不明白,“你是说,我前脚入宫,你后脚就忙不迭写了信送去?”
知音点头。
时蕴头一次为这般高效率办事感到头疼。
知音安慰道:“山长名望摆在那,不至于真逃,指不定会派永安王来为你求情。”
时蕴抬头看她,一脸生无可恋。
知音知错垂下了脑袋,嘴里嘀咕,“虽然永安王殿下打小欺负你,但真关乎性命,他没有不来的道理。”
问题就出在这,如果真出了事,永安王作为皇亲能说的上求情的话,可以救场。
可她现在没事了,永安王再来,那就是来拿她寻开心的。
永安王是贺岐表亲,早年协助贺岐夺权有功,赏了块封地,同时他也是时蕴同窗,为人极其不讲道理。
她迄今都还记得,那年冬天祝长晋给她一脚踹河里,美其名曰她身子太弱不像个男子,要多磨炼。
害她裹着被子,打了三天喷嚏。
想起来就觉得牙痒痒。
“你赶紧再传书去,告诉夫子不用管了,千万别让他来。”
时蕴起身,想回屋去先休息会。
倏然想到什么,停住脚步回头看她,“今日蔺奕湘是不是来过?”
知音:“是,就早一会来的,我当时急哭了,给他说您被陛下召去了,他脸色顿时白了,二话没说就走了。”
时蕴蹙着眉头想了一路,也没想明白他心里怎么想的。
朝堂上。
皇帝还没现身,诸多臣子交头接耳,无一例外,都是说陛下终于开始为江山社稷考虑了,昨天的折子全给批了。
往日堆上去的,百来本里面也就一两本被批过,足以见得贺岐格外没有耐心,翻了两册最上面的就不看了。
唯独时蕴的,即便压在底下,贺岐也要翻出来看。
倒不是他多在意时蕴的政见,而是时蕴向来有想法都是直接跟贺岐开口,但每日都要交折子走过场,她往往会一番涂涂画画,敷衍着交上去。
本是料定了贺岐不会看,结果他头一个就是把她翻了出来,看见她画的四不像,笑得人仰马翻,哪里还有当皇帝的样。
也不责罚她糊弄,反而享受这种每次打开她折子都是不同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