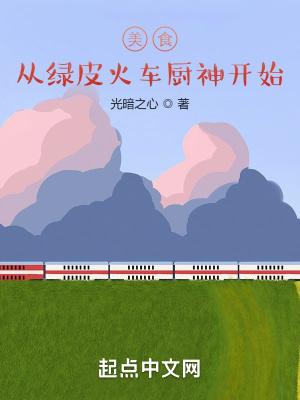UPU小说网>主公别消我免广告 > 第40页(第1页)
第40页(第1页)
崇云考是国相,有开幕府的权利,按理来说应该在自己的国相府办公。但游雍刚刚入主司州,民心还不稳定,不好在此时大兴土木,因此崇云考现在在长安都没有自己的国相府,充当临时办公室的,是雍王宫一间名唤“东阁”的小宫殿。
白未晞没有接受游溯的印绶,现在理论上还是白衣一个,连开幕府的权利都没有,因此游溯将东阁对面,一间名唤“西阁”的小宫殿划给白未晞,充作白未晞的办公地点。
整个雍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就在这看起来狭小又破败的东西二阁中诞生,也因此,崇云考被人称为“东相”,白未晞则被称为“西相”。
杜望来到东西二阁的时候,正好看见崇云考和白未晞都在东阁对坐饮茶,陪坐的是如今的左丞桑丘。三人说说笑笑,桑丘的脸上更是一派笑意盎然。
杜望动了动鼻尖,闻出来三人喝的茶是六安瓜片。
六安瓜片是两淮名茶,产地六安现在正处在王师和楚军交战的战场上,以至于六安瓜片现今极为难得,已经被商人炒到了天价。
杜望想到自己每天为了粮食茶饭不思,这几人竟然还有心思喝茶,一时间满心泛酸:“几位当真好雅兴。”
说着,杜望一一给几人行礼:“见过国相,左丞,白先生。”
几人都给杜望回礼,崇云考邀请杜望入座,声音不咸不淡:“府君大人近日以来看起来颇为憔悴啊,最近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我遇到什么难事你不知道吗?
杜望心里咆哮。
宝宝心里苦,但宝宝说了:“下官为何事为难,难道国相大人不知吗?”
这话说的实在是酸涩极了,像是一个无辜少女正怨怼着她没良心的情郎。
崇云考闻言哈哈一笑:“府君大人说笑了,你出身京兆豪右,说动京兆豪右出钱出粮抗洪救灾还不是手到擒来?”
杜望只觉得自己就像浑身上下都泡在了黄连汤里,就连每一个呼吸都是苦的:“国相大人别挖苦下官了,下官要是要的出来粮食,还会像如今这般夜夜辗转反侧吗?”
他指了指自己的头发:“国相大人看看,下官的头发都白了。”
崇云考仔细看去,还真让他发现了杜望头顶几根显眼的白发。崇云考当时便大义凛然地说道:“老夫知道,从豪右之家要钱要粮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府君大人必然为难。但是老夫也难,咱们就都勉为其难吧。都是为主公做事的,大家理应同舟共济,府君大人需要老夫做什么,尽管说出来。”
杜望:“……”
杜望恨不得吐血。
勉为其难?
你勉为其难什么了?
勉为其难地在这里悠闲喝茶还配个红泥小火炉?
话说的是真好听,就是仔细一琢磨,什么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
杜望心里骂骂咧咧。
白未晞拢着身上的狐裘,也慢条斯理地对杜望说:“府君大人有话不妨直说,我等虽然对司州人生地不熟,但总归不会看着府君大人一个人难的。”
杜望想说的话就这么憋在了嘴里。
好好好,你们人生地不熟,就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长安人干活是吧?
杜望也算看明白了,这几个人根本不想掺和进管司州豪右要粮的事。
也是,雍王是想长久待在司州的。想要黎民百姓的信服,这次洪灾就不能不救;但想要长久地统治司州,就不能和豪右搞得太僵。
权利从来都是自下而上的,没有司州豪右的认可,雍王溯只怕连治理司州的小吏都找不出来,又何谈让司州成为雍王的后盾?
现在雍王又想从豪右口袋里掏钱赈灾来损有余而补不足,又不想因此让司州豪右产生什么想法,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杜望这个同为司州豪右的本地人去得罪其他的司州豪右。
这样一来,雍王集团和司州豪右见面还能三分笑,被他选中的人也会因为成功在雍王集团中央站稳脚跟而对雍王溯更加忠心。
要不是现在受苦受累是自己的,每天头秃的也是自己。杜望都恨不得为雍王殿下的手段叫声好。
但事已至此,杜望看上了雍王这艘船想上,那不管游雍集团给他开出的船票价格多么的高昂,杜望也得咬牙买。
因此杜望咬咬牙,咬得牙都碎了:“无妨,不是什么难事,下官没有什么困难,一定会将这件事为主公办好。”
杜望的话音刚刚落下,崇云考就迫不及待地说:“那老夫就替司州百姓在此谢过府君大人了。”
杜望苦着脸走了,临走之时的背景煞是萧瑟,仿佛秋冬之际无依无靠的落叶,让人忍不住为之悲叹。
待杜望一走,崇云考顿时敛去了刚刚那副老油条的样子。他摸着自己长长的黑髯,意有所指地说道:“不愧是几百年的大家族,就是与众不同。”
桑丘点头:“白先生说的果然没错,涉及到自身利益,他们竟是连和京兆韦氏的通好之谊都顾不得了。杜府君都没办法从司州豪右口袋里掏出粮食来,若是换作是下官,就只能建议直接抄家了。”
人与人之间最坚固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京兆杜氏想换的雍王溯的信任,却要京兆其他豪右出血,那怎么可能?
要粮之事一过,这些本就是置散沙于一器的京兆豪右之家,之间的联盟只怕要如流沙之水了。
想到白未晞接下来的计划,桑丘对白未晞深深行了一礼:“白先生的计谋天下无双,必然能让司州豪右争先出粮。”
白未晞一点也不居功:“白某不过提了个主意罢了,具体实施还要看左丞大人的,此计能不能成功,全看左丞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