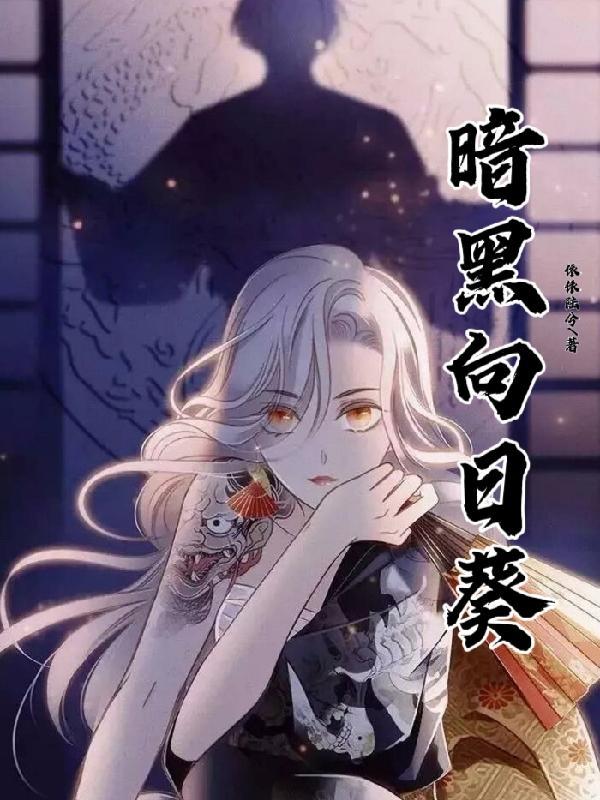UPU小说网>主公别消我免广告 > 第51页(第1页)
第51页(第1页)
他的沉默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明哲保身,而不是在否认这个提议。
游溯又问桑丘:“左丞的想法是什么?”
桑丘出列,他张了张口,却什么都没说出来,最终只能颓然地低下头。
游溯的眼中闪过浓浓的失望,他又问杜望:“右丞也无言以对吗?”
杜望深深作揖:“臣有罪。”
游溯都要被这些人气笑了:“你们别告诉孤,雍国朝堂面对时疫,只能想出来这么个方法。”
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直面游溯的怒火。
游溯深呼一口气:“白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此时落在了白未晞的身上,那些目光充斥着复杂,似乎是又想白未晞能拿出什么方法来,又觉得若是真的让白未晞拿出解决办法,他们的脸上实在是无光。
白未晞出列对游溯作揖,说道:“臣以为韦大人言之有理,当务之急确实是先将疫民隔离。”
朝堂上刹那一静,这一刻,所有落在白未晞身上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变成了惊讶,似乎是没有人能够想到,仁政爱民的白先生,竟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游溯瞪他:“白先生!”
白未晞叹了口气:“主公,方案不是一时就能拿出来的,总要时间。”
听这语气,白未晞是打算抗疫的。
游溯松了口气,但这句话却引来了韦由房的责问:“白先生,这是时疫,方案可容不得你慢慢想!你要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有人感染时疫,一旦没有及时管控,整个长安甚至京兆,司州都有可能变成一座死城!”
这就是这些肉食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牺牲这些疫民的原因。
在时疫面前,天生的王侯将相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们和普通黔首也没什么区别。时疫不会因为他们出身尊贵而对他们网开一面,死神的镰刀会无情地收割所有人。
当引以为傲的阶级无用之时,天潢贵胄开始恐惧了,韦由房毫不留情地开口道:“白先生,你要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黔首,让长安变成一座死城吗?”
白未晞的声音也冷了下来:“白某何时说过,会让长安变成一座死城?”
“你现在的行为,就是拿所有人的命去赌!为了一群低贱的黔首!”韦由房近乎暴怒地质问,“难道在白先生的心中,那些低贱的黔首比我们所有人的命都贵重吗?”
“几千黔首而已,因时疫而死,谁能说出半句不是?”
“韦大人,你的祖先也曾是黔首!”白未晞的眸色彻底冷了下来。
韦由房反唇相讥:“韦某的祖先乃是夏禹之后,豕韦彭祖!”
“但夏禹也曾是黔首!”
韦由房一愣。
白未晞毫不犹豫地打碎韦由房最引以为傲的东西:“远古时期,天下经三皇,过五帝,夏禹虽为黄帝之后,难道没有曾为黔首的先祖?”
“太康失国,大羿僭位之时,少康难道不也是区区一黔首?”
“豕韦失国后,韦氏一族又当了多少年的黔首?”
“韦氏先祖筚路蓝缕方有今日之京兆韦氏,难道先祖的栉风沐雨,就是为了让韦大人今日在此大放厥词的吗?”
“你……”
韦由房失礼地指着白未晞,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白未晞没有理他,而是用冷冰冰的目光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扫视了一遍,直到所有人都在他的目光下低下头来,白未晞才一个接一个地质问:
“国相大人,白某记得,陇西崇氏的祖先在大晋开国时是一介屠户?”
他的目光落到桑丘身上:“左丞大人,你的先祖在追随高祖之前好像是位引车卖浆的商户?”
他又走到杜望面前:“右丞大人,京兆杜氏是在武帝时期发家的吧,那时京兆杜氏的先祖甚至是一介赘婿,在征战时被优先征发,才因在战场上战功赫赫而开创京兆杜氏。”
望着一个个低下头的天潢贵胄,白未晞用堪称嘲讽的声音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道理,白某以为诸位早该懂得,怎得如今认了个从未见过的祖宗,就瞧不起自己的出身了?”
当年晋高祖不过也是个黔首,在秦时做着微末小吏,响应着那位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侠士,揭竿而起,竖起反秦的旗帜。
只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短到说出这句话的人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了新的王侯将相,还想要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成为王侯将相。
当新的王侯将相诞生的时候,他们便开始由衷地期待王侯将相是“有种”的,不想另外的自己学着现在的自己一样,反抗自己打下的帝国。
所以大晋的高祖认了高贵的祖先,他的身边那些屠户,商人,地痞流氓通通摇身一变成了圣人之后,你认这个祖宗,我选那个祖宗,然后扒拉扒拉算算,咱们都是高贵的贵族。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笑话。
但是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白未晞没有再理这些被他怼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王侯将相,他转身对游溯说:“《尚书》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民不宁,则天下不宁;天下不宁,则君王不宁。”
“诸位可还记得,朝廷南渡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失去对北方的控制的?北方诸王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控制了整个北方的?”
“是民心所向!”掷地有声的声音炸裂在每一个人的耳畔。
“大河动荡,遗祸兖,幽,青,冀,徐,司,并七州,使燕地,齐地,楚地,雍地之民在一夕之间无家可归,造成的流民何止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