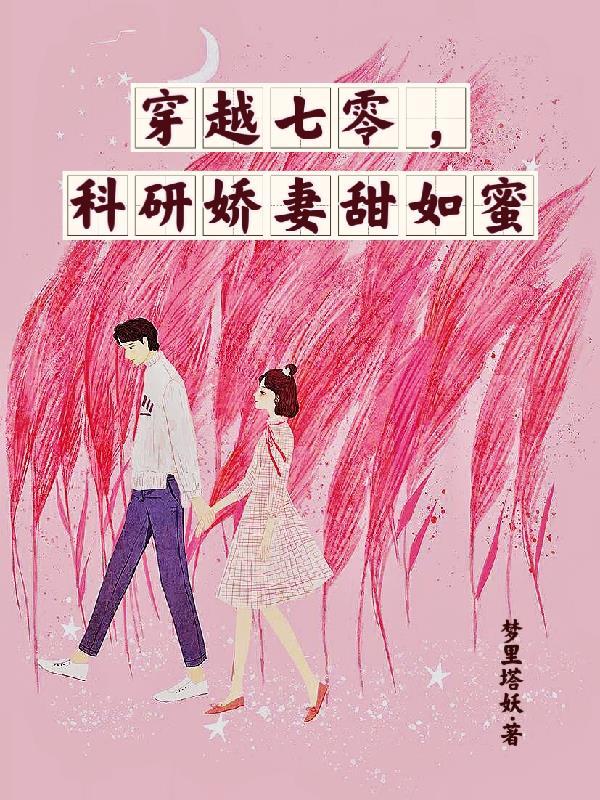UPU小说网>权臣沙漠 > 除夜共欢一(第1页)
除夜共欢一(第1页)
将那人皮面具收好后季舒这才吹了个哨子过不多时大白便从远处奔了过来。
骑在马上的沈浥尘老远便看见了她这副狼狈样,此时近看更觉惨烈心中说不出是何滋味哪怕瞧见她背后的长匣都不觉喜悦了。
季舒却管不了那么多,谁知道曲华良回去后会不会派人来追?赶忙跨上了马,扯着缰绳便疾驰而去。
“真是没想到,皇后竟是在御林军中安插了那样的人手。”想到刺穿自己手臂的那把龙泉剑,季舒便忍不住一阵感叹,“能持有龙泉剑的人,除了御林军将军外就只剩两位中郎将了,他们哪个不是被凌绝视为心腹?”
“皇后这一颗暗子布得妙啊指不定哪天就能在背后捅凌绝一刀子。”季舒说着不由摇了摇脑袋她此次夺画虽是有意遮掩混淆了一番但依着皇后的谨慎头脑必然已经对她的身份有所怀疑了不过好在最后将这画像给弄了出来,不然可真是亏大了。
季舒自说自话了好一会这才现沈浥尘的异常。
“你这是怎么了?得了世婶的画像不高兴吗?为何一句话也不说?”
季舒见她仍是不说话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向前挪了挪身子想要凑过去看她的脸色。
沈浥尘察觉到身后人的靠近却是僵硬着身子偏开了头。
季舒长眉一皱还以为她是不喜自己身上浓郁的血腥气只得又向后边退了些,其实她自己闻着也挺难受的,更别说衣衫上浸透的血液被寒风这么一刮,早被冻成了冰块一般,穿着着实硌人。
“此处不方便,一会我回梅庄收拾下就好了。”
沈浥尘红唇紧紧地抿着,看着越沉静。
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之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中。
“你不至于这么嫌弃我吧?一句话也不说。”季舒左思右想愣是没明白,感觉她似乎有些生气,又想不通原因所在。
沈浥尘听着这话不知怎的鼻头忽然一酸,呼吸瞬间便乱了,微微垂着头,双手紧紧拽着袖口。
季舒等了许久,伸指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她的肩,试探性的问道:“你,不会是在愧疚吧?”
见她仍是不答话,季舒心里估摸着自己应该是猜对了,顿时有些好笑的掰过她的身子,“你个闷葫芦,有什么直说便是,竟还要我来猜。”
沈浥尘呼吸一滞,这才扯着嘴角说道:“你的伤……”
季舒看她这欲言又止的别扭样笑得越开怀了些,摆了摆手道:“我这身上的血都是别人的,这要真是我流的,我早疼得在地上打滚了。”
沈浥尘瞥了眼季舒一直垂在身侧的左臂,一时有些着恼,“我与你说正经的。”
季舒把笑一收,从善如流地板着张脸道:“我这身上的血都是别人的,这要真是我流的,我早……”
看着沈浥尘那直勾勾的眼神,季舒舌头一卷赶忙改口道:“有一点点是我的。”
沈浥尘咬着下唇,心中又气又疼,整个人看着便越沉闷了。
“哎,你这表情看着怪吓人的。”季舒脖子一缩,弱弱地解释道,“伤的真不重,就是看着惨了些。”
沈浥尘表情软了下来,柔声道:“可是敷了伤药?”
季舒生怕她不信,点头如捣蒜“一早便敷了,现下都感觉不到疼了。”
沈浥尘叹了口气,只得说道:“那我们快些回庄子上吧,你这身上的伤得赶紧处理下。”
季舒依言催着大白加快了度,两个时辰后便回到了梅庄,季舒将那长匣交给沈浥尘,而后便回了自己的屋内。
吩咐下人送来热水后,季舒先是脱去了外面穿着的夜行衣,可到里边的中衣时却犯了难,手臂上的伤口和衣衫已经沾粘到了一块,因着气温冻得紧紧的,方才没感觉到多少疼痛,现在却是受罪了。
硬扯下来是不行的,只得取了些温水浇在上头,逐渐软化凝结在一块的肌肤和衣物,偏偏这个过程又会刺激到伤口,无异于钝刀割肉,简直比再挨一剑还难受。
待衣物完全剥离下来后,季舒脸色惨白不说,额上满是大汗,她这手臂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伤,内里筋骨都被剑气伤着了,怕是得养好一阵子才能恢复。
先将手臂上的伤口清洗干净后,季舒这才爬进了浴桶中,将受伤的左臂架在桶边上,用右手擦洗身上的血污,没多久木桶之内便尽是血水了。
“吱呀”一声,房门突然毫无预兆地被推了开来。
沈浥尘看着正泡在桶内的季舒,先是一怔,随后还是拿着纱布和伤药行了过来。
“你、你都不敲门的吗?”季舒被这么一吓,赶忙将身子沉入了水中,除了受伤的左臂还架在桶边,就剩了颗脑袋在水面上。
沈浥尘倒是一点不自在也无,“我没料到你在沐浴,再说你是男子,有什么好怕的。”
“我……”季舒脸红得不行,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慢慢将头扭到了另一边,小声道,“谁说男子就、就不怕了?”
沈浥尘没理她,看着桶内有些浑浊的血水,蹙眉道:“我让下人来给你换水吧。”
“别!”季舒赶忙又将头转了回来,察觉到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又补充道,“我的意思是不用麻烦了,简单收拾下我们还是先回府,待在这到底不大安全。”
沈浥尘也没再坚持,看着季舒那白皙手臂上狰狞可怖的伤口,什么也没说,俯身拿着干净的布巾动作轻柔地拭去了伤口周边的血液。
她的脸离得很近,季舒甚至能清晰地数清她的眼睫毛,还能嗅到不同于自己身上的清雅幽香,不怎为何,对于沈浥尘,季舒时常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