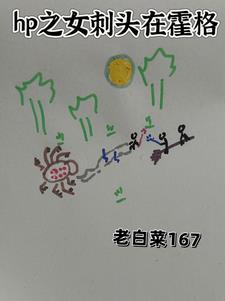UPU小说网>后宫生存游戏 > 第廿九章赐死荆王(第1页)
第廿九章赐死荆王(第1页)
八月微凉生枕簟,金盘露洗秋光淡。
八月里,正是我身怀六甲之时,虽已至立秋,却仍是燥热不堪,每日都得命人从御膳房取些冰来给我降暑。
自上月因泉州大风一事填充了国库后,樘便鲜少再有愁云。只因我那日一计之故,便常闻得有人在背后褒奖我,说我同当年先皇的万贵妃一样,都是独宠六宫,却是与她有莫大的区别,更是有人说,皇后娘娘就是大明朝的福星,是皇上的福星。如此,着实叫我盛情难却。就连樘,也时常拿此事来调侃我。
是日,我正逗弄着照儿的小脸,忽闻得几声悉悉索索的动作,迎声望去,只见母亲领着紫苑提着一包东西奋力走进。
见桌案上端放着酸梅汤,母亲慌得跑来拿起酸梅汤,“诶哟,我的祖宗诶,都六个月了你还吃冰的,快别吃了1我微蹙眉头,“诶呀娘,你干什么呀,你看这天儿热的,我就不能吃点儿东西消遣消遣?还有啊,你带回来的那是什么呀,你看你把人紫苑累得1“陶土啊,你刚生下照儿那会儿不是很喜欢陶艺,怎么现在突然不玩儿了?。”听得‘陶艺’二字,我忽的冷下脸来,沉声说道:“我那会儿是挺喜欢捏陶,可如今每每见到陶土,便想到故去的陶艺,此皆是我种下的因果,你要我如何玩得安生?”提及陶艺,母亲亦是冷下脸,良久,终是轻叹,“娘这不是看你整日
里无聊得很,就想去尚服局取些陶土回来给你打发日子,哪知你这般忌讳她的死。”“好了,紫苑,你把土放在这儿吧,你们都下去吧,本宫想一个人静一静。”“是。”见母亲与照儿仍在屋中,我着实苦恼,也不好叫母亲出去,只得俯身,“照儿,你也同姥姥一起出去玩儿好不好?”“好。”捏了捏他的脸,便推着他的脑袋瓜子,“去吧。”只见他拉起母亲的手,奶声奶气的说道:“姥姥,我们出去玩儿吧。”也着实佩服照儿,早在二十月时,便已能同两三岁的孩子一般正常言语,只是有些结巴与模糊罢了,但无论如何,我这个做母后的,到底还是能大概听懂些。
母亲忽的沉下脸,直瞪着我。
屋中终是只我一人,我不禁惋叹,当年陶艺的死,算到头来,还是我种下的因。说来惭愧,此事本已是一个错误,至后来,她枉死在鹤龄手下。而我,却是百般包庇,处处维护,如此果,便是我在心底默默承受。
本已是将陶艺的死忘却在脑后,今日母亲又提及‘陶艺’二字,陶艺啊陶艺,你为何要取个这样的名字,惹得我一见陶土便是万分惆怅,如今更是弃了我曾经最爱的陶瓷手艺。
带着无比凝重的心情,漠然走向瘫在地上的陶土,伫立在旁,不禁又是一声叹息,陶艺死时场景皆历历在目。忆起当年初识陶艺时,便觉她长相清新
脱俗,乃为世间少有的绝尘女子,亦是聪慧过人,大方得体,只可惜天妒英才,叫她年纪轻轻的,便已逝去生命。
已是许久未碰陶土,都已生疏了许多,抓起一把陶土,心中又是一阵遐想。
忽闻得一阵开门声,才见是樘,见我手中抓着一把泥土,不觉一阵困顿涌现脑海。
“怎么了,不开心?”我放下陶土,长吁一气,“没有,我只是忽然想到了陶艺。”他愣住,神情亦是凝重,终还是佯装作轻松的模样,侃笑道:“怎么,睹物思人了?”“呵”,我冷笑道:“陶艺的死,都是我种下的因果,当年若非我提出要将陶艺赐婚于鹤龄,她也不会难产而死,这都怨我。”“你瞎说,当年你也是出于一片好意,这怎么还成了你的错,你别总把那些莫须有的罪责都往自己身上揽1我不语,只黯然沉思,良久,终是凝着他,“樘,其实我心底还藏着一个秘密,这两年总想找机会告诉你,却是一直都不敢开口。”“是什么惊天的秘密,竟连你都不敢开口?”我略有些迟疑,终是长吁,“其实……”我欲言又止,虽是信任樘对我的爱,可此事关乎张家存亡,一旦说出,轻则,鹤龄被问斩,重则,怕是要惹得张家几代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此果,亦是覆水难收。
顿了许久,樘似是有些忍耐不住,“到底是什么事,为何连你都不敢同我说。
”对于此事,我本是无意,可如今若不说出此事真相,我便是寝食难安。我紧蹙眉头,“其实当年的陶艺的死…”“别说了!”他猛然打断我,“大家心中都已明了,只是都不愿道出,如今你又何必揭穿,不是惹得人没情面了?”我一阵怔忪,满目惊惶的对上他的眸子。
屋中一片沉寂,良久,他终是拥我入怀,“没事了,都过去了,还念着她作甚。”我惊惶,不只是因为惊诧于他知晓此事,也是因有人出卖我。当年知晓此事的,若非我张家人,那便只有云袖,原来这么多年,我还是信错她了。
“还记得去年答应你的,要为金夫人修一座宫殿。”我怔然凝着他,静待他的言语。
“本是答应你,在初春时节开始此项工程的,却是因黄河绝提一事给耽搁了,如今泉州之事也有了些不错的进展,现正值立秋时节,这秋高气爽的,倒也适合修葺宫殿,前几日我也命工部侍郎徐贯在京中物色了些瓦匠,择吉日开始动工。”我轻推开他,佯装作不悦的模样,略带试探的口气问道:“你要为我娘修建宫殿,难道朝中的大臣就没说什么?”“这倒没有,你可是我大明的功臣,是福星,还能有谁对你不满的,何况如今国库金银无数,财产过多,这也都得归功于你,不过是为你母亲修座宫殿,他们能说什么,你太多虑了。”我冷笑,“谢迁向
来对我有诸多成见,这两年我可是什么事儿都尽量避着他的眼耳,你可也得避着点儿,若是再让他知晓了,怕是我又得遭他指责。”“区区一个谢迁,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呀,就是多心了。”“你净如此,区区区区,谢迁那张利嘴,可是敌过我千万张嘴,虽已是过了好些年,可他当初说我将来会祸害你,祸害大明江山,此事我可还是记得清清楚楚。”他讪笑道:“好啦好啦,他那也都是气话,你看你,到底还是为我大明江山做了不少好事,又何必在意他当年无心之言呢。”“说得倒是轻巧,可若是换作你,定然也是如我这般记恨他”,我喃喃道。
“诶,你可还记得当初荆王谋反之时,那会谢迁顶撞他,我可是听沈……”他忽的顿住,“听人说,是你来得及时,救了他一命,如今他该是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还会对你有成见。”“你听谁说的?”我怒目瞪视他,“我方才可是听得清楚,沈什么,沈琼莲?”他支支吾吾,似是极为躲闪,我终是耐不住性子,满是嘲讽的问道:“怎么,你与她还未撇清,还是藕断丝连?”他扯住我的衣袖,“这怎么敢,都有你了,我怎还会想着别的女人。”我甩开他的手,故作高傲姿态,“知道就好1他忽一声轻叹,确是惊了我,我竟以为他是为我处处约束着他而叹息。
“你,怎么了?”“
昨日皇祖母找我,只因荆王上次谋反一事仍为我不平,硬是要我将他处死,可我…”他仍是叹息,“你也知道的,当初我可是答应了不杀他,君无戏言,如今皇祖母之命,我亦是不可违背,这,可是叫我好一阵纠结。”我一阵讽笑,“单是为了这个?此事倒也简单,既然是皇祖母要你杀的,那就借她的懿旨来处死荆王咯,你又何必如此犯难,瞧你那脑子,怎会这般不灵光,这皇帝让我来当好了,至于皇后嘛”,我搂住他的肩,坏笑道:“就让你来做吧。”“别闹了,皇祖母的意思你也并非不懂,她知我下不去手,这话里话外,净是要我亲自动手的意思,你要我如何推脱。”太皇太后这般痛恨荆王,想必不单是为荆王谋权篡位一事,更多在意的,该还是因荆王挥刀刺杀樘之事,樘自六岁起,便是由她抚养。如此,她定是尤为心向樘,仅在每年乾清宫家宴时,四弟向她敬酒时她的神情中就可看出,她对樘的爱,超乎所有人。因而,她对荆王,必然是恨之入骨。
每每有人提及荆王挥刀刺杀樘一事时,我便忆起他与沈琼莲曾有过的一夜之欢,心头便又是一阵咬牙切齿的恨意,冷冷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如她所愿,亲自动手又何尝不可?”“又来了,我就知道,一提起荆王与沈琼莲,你便要同我生气。”我抽搐起嘴角,“怎
么,你还不乐意让我说了,当年若非你出去跟她厮混,我们如今会只有照儿这一个孩子?”“好好好,咱们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先说说荆王的事,我如今正为他的事愁着呢,你得给我想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她都说了要你亲自将他处死,要我能如何,难道要我随便找个人替他死?”他忽的灵光一闪,“这个好,那就找个将死之人做替死鬼。”“好什么呀,你不挺聪明的,天下你都治得好,怎么今日就让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给绊住了,还真是糊涂。”“那不如,你替我去杀他,杀他并非我意,你持皇后懿旨,便可轻而易举便将他赐死。”“我?朱樘,我不过区区一个女子,怕是连刀都拿不稳,你还要我斩了他,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他背过身去,“非也非也,杀人之法有千百种,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腹蛇野葛,以其羽划酒中,饮之立死。”“原来你心中早有计策,今日来此,是因心有借刀杀人之故。”他回过身来,“聪明!”“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要我做任何事都可以,可这是杀人哪,你下不去手,我更下不去手。”“柔儿!”他扯住我手臂,“只这一次,你只需下道口谕,再与我一同去趟天牢就好,至于赐酒一事,自然还需得我亲自动手。”我仍是不予理睬,他便缠起我的衣袖,
“只要你帮我这个忙,日后不论是什么事,我都答应你。”我顿了顿,不过是要我下道懿旨,于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这般轻而易举之事,便可得道日后莫大的待遇,也未尝不可。
“好!”东厂大牢:
依旧是那般昏暗不见天日之地,依旧是那般恶臭叫人压抑之气,只见云袖端持着御赐鸩酒,同我与樘,皆是带着略微凝重的心情迈进关锁着荆王的牢笼之中。
“荆皇叔,好久不见”,我冷笑道。
他悠然抬头,瞧见我与樘,均是置之不理,透过我们二人之间,才瞥见伫立在我身后的云袖,手中的酒与杯。
终是冷笑,那笑容,甚是惨淡,更是叫人不禁毛骨悚然,“今日这刮得是什么风,怎么把你们两位吹来了,可真是叫我这天牢,蓬荜生辉啊。”“昨日暹罗进贡了美酒,听闻荆皇叔您素爱暹罗美酒,今日,便特来赐酒一杯。”“哦?那还真得多谢娘娘的盛情了。”话音未落,便已见樘转身倒好鸩酒,举在荆王眼前,这步步紧逼,着实叫空气凝结,窒息之感油然升起。
他轻笑,“这是鹤顶红?”“不,这是鸩酒”,我说得云淡风轻,似是毫不吝惜他人性命。
他执起酒杯,一声怅然轻笑,“我死并无碍,只是,我荆王子弟…”他凝着樘,“毕竟他们与你,还是近枝,若他们没有同我一样,犯下这谋逆大罪,是否还可留着性命?”“嗯
”,樘微微颔首。
他终是举杯饮下,毫不畏惧,落得个饮鸩而亡的下场。
弘治六年八月十三日,令朱见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