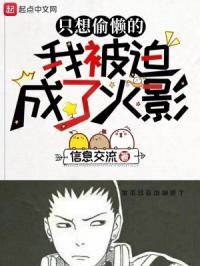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前任对我恨之入骨免费最新章节更新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时过今日,这个女人对于她来说就像是被蛀空了的牙齿,不尖叫不疯魔的时候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只是风吹来的时候隐隐有些酸痛。
今天这阵风来得够猛烈,把高三统考的压力一股脑的包裹了起来,像是一粒粒细碎的石子,生疼的拍在了别栀子的脸上。
——我让你生我了吗?
——你以为我想天天被人戳着脊梁骨叫婊子养的东西吗?
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上头的情绪会无限放大你内心曾经滋生过的所有阴暗面,宣泄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本能,再勇猛的人都会有脊梁骨崩溃的那一下。
而现在别栀子就在那道情绪的边缘徘徊,怒火和愤然的对骂在唇齿间来来回回的过了一下,最终又被她完好无损的咽了回去。
看不出这只外表像兔子一样脆弱的女孩,年纪小小就已初成铁石心肠。
好在有人听见了深夜理发店二楼传来的巨响,那年的通南县只能算得上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县城,这一块的鸭肠小道就是当时整个通南县最穷的地方,拥挤的房屋一打开大门,家家户户都相连着。
——咚咚咚
夜里的敲门声压制了门内蓄势待发的火山,随之而来的是隔壁老张关切的问候。
“悦容啊,没事吧?家里怎么那么大响儿呢?”
男人短短的一句问候,像是陡然关闭了别悦容身上神经质的开关一样。
许是情绪转变得太快,脸上的肌肉还没缓过来,剎那间显得这张粉面堆砌的脸有些许扭曲。
“张哥——我没事儿,我教小孩儿呢!”
她立马忘掉了屋内僵硬着身子的别栀子,捏着嗓子扬声道,又一边以最快的速度补了个妆,踩上红高跟,笑着开门迎她的新发展对象去了。
别栀子站在原地,冷眼看着隔壁那位经常在校门口摆摊卖面的老张,一脸羞涩的从嘴里说着“这不好吧大晚上的”、“就是担心你们孤儿寡母的来看看”、“我就不进去了吧”,一边被女人婀娜的身姿缠了进来。
“栀子多大了?”老张干咳两声道。
“哎呦,十八了,不听话可愁死人了。”别悦容那副恰到好处的愁容,跟她花容月貌的寡妇形象很搭边。
“在哪上学呢?”
“好像叫什么通南一高的。”
“嚯,这可是重点高中,真聪明啊这孩儿!”
别悦容压下翘起来的嘴角:“什么重点高中,还不是交钱上学。”
“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儿啊有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吼,得靠讲道理。”老张在别悦容这里找到了被需求的感觉,顿时滔滔不绝了起来,“我们家小孩就跟栀子差不多大,她妈就从来不吼,你听哥说,小孩这个年纪正好是叛逆期知道吧,咱们做家长的……”
看了半天,t别栀子一句话没说,转身回房间“哐当”一声带上了门。
门外时不时传来女人娇俏的低笑,过了一会又变成了男人爽朗的笑声。
别栀子有时候也很佩服她,手底下的男人们,即使拥有美满家庭,有妻有儿的,也能在她的三言两语下拜倒,活像是白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遇见红颜知己一般迷恋。
“是吗张哥,你可真厉害。”漂亮女人崇拜的视线变成了老张的兴奋剂。
“你一个人拉扯孩子也不容易,我看着栀子也乖巧,”老张的视线飘忽不定起来,油光光的面孔上泛着红光,“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加个微信尽管找哥。”
今天没有晚自习,别栀子也没能吃上晚饭,她贴着墙根站,这会空荡荡的胃里却隐隐作呕,像是沸腾的胃酸在一个劲儿的往外鼓着泡泡似的。
空气又潮湿又闷热,狭窄的房间里仿佛被雨水泡发过一样,充斥着难以言喻的腐朽感,窗户打开也无济于事。
只好靠在墙角的阴影里闭上眼睛,聒噪的调情声变成一阵悠远的杂音,屏蔽在了脑海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凉风从旁边大开的窗口吹进了逼仄的卧室里。
薄薄的眼皮感受到了刺透皮肉的光感,像针一样扎进了别栀子的眼睛里,她睁开眼睛。
紧闭的房门被人从外面随意打开,别悦容一脸嗔笑的挽着老张的手臂,一边朝着别栀子热情招手道:“来来来,跟你张叔说说平时在学校怎么考试的,他屋里小孩就愁分数呢!”
这个女人变起脸来,有时候让别栀子都觉得胆战心惊。
漆黑的卧室打进来一束扎眼而突兀的光,像是毒蛇一样从门外游走到了穿着睡衣的别栀子的身上,她下意识的想要退后一步,背脊却已经死死的抵住了墙壁,退无可退。
老张是典型的中年发福男人的长相,别栀子平日里在校门口吃早餐的时候,只觉得这人两颊有肉,下的青菜面好吃,看起来也怪慈祥的,大抵是个有福的长相。
这会儿双脚踏在她卧室的地板上,两坨肉从鼻翼两侧凹陷了进去,毛孔粗大泛油光,滴溜溜的眼珠子在宽大的眼眶里瞎转悠,像只半死不活的癞□□。
两人向她投来的笑容瞬间变了个样儿,恍惚间腐烂的黑斑一点一点的爬上了他们的肌肤,发脓的疮口挤压着五官,笑容扭曲在了变形的脸颊上。
大热天的,别栀子背后起了一身的冷汗。
“你这孩子,说两句啊!”别悦容被扰了兴致,不耐烦的催促道。
月色下,躲在墙角的别栀子咬紧牙关,一双带刺的眼睛看着俩人,冷声道:“出去!”
空气安静了几秒。
“哎呦,栀子要休息了,咱们还是出去聊吧。”老张眼看着气氛不对,连忙站出来打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