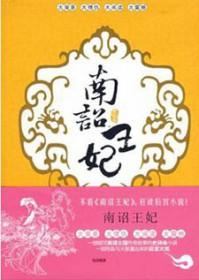UPU小说网>别在酒吧后巷捡对象剧透 > 第59页(第1页)
第59页(第1页)
钟煦呈的照片就在最上方偏左侧的位置,穿着白大褂,面容沉静俊美,眼睛冷淡漂亮。
岁月似乎格外偏爱他,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张脸还是一如既往地年轻和好看,与十七八岁时并没有太大区别。
晁凌山盯着那张照片看得出神,直到感觉有人从身后经过,才转头喊住了装作没看到他的钟煦呈:“小呈。”
钟煦呈脚步未停,直接迈着长腿走进办公室把门一关,拒绝交谈的态度表现得分外明显。
晁凌山望着那扇紧闭的门十分失落,越想越觉得不甘心和嫉妒。
他当年不过是一时糊涂走错了一步,钟煦呈就记恨那么多年。
那个叫庭钺的臭小子诸多隐瞒形迹可疑,钟煦呈却还是把他当宝贝一样捧在手心。
当真是不公平。
不对,如果钟煦呈知道他现在那个男朋友做过什么,一定
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翻脸,就跟当初对他一样。
晁凌山不禁为自己先前的莽撞和死缠烂打感到后悔,他觉得自己应该再沉着一些,等这两人闹翻了才出手。
一墙之隔的办公室里。
钟煦呈拆了筷子开始吃午饭,晁凌山的突然出现并没有影响到他的食欲。
他不会阻止林丛盛继续和这个人合作搞医疗器械生意,也做好了对方会随时来医院走动的心理准备。
只不过他有时候会非常厌烦晁凌山的态度,那种拿捏着诱饵故作情深,在等他自动送上门的自负,让他觉得无聊又可笑,导致他不止一次怀疑自己当初的眼光为什么会差成这样。
庭钺的电话打来的时候钟煦呈正准备午睡,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很小的隔间,之前是杂物房,后来有段时间总是加班,他就把里头收拾出来,摆了张可折叠的单人床。
“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低沉柔软的声音透过听筒传入耳中,钟煦呈先是感觉耳骨上敏感的神经稍稍颤了一下,然后才慢慢适应庭钺声线里自带的渣苏感。
“你问这话让我怎么回答?”他心情放松地跟庭钺聊天,“你想听什么答案?”
“就这么回答啊,”庭钺轻笑着教他:“很想,想硬了。”
钟煦呈学不来他的不正经,无奈地喊他:“庭钺。”
“我在,”庭钺又乖又甜地应他,“师兄有何吩咐?”
“你特意打电话回来就是想调戏我吗?”
“不是啊,”庭钺唇角噙着淡淡的笑,目光轻轻移动,一边往拉着帘子的急诊室看了一眼,一边低声开口:“师兄,我今晚有点事,要在u城过夜,可能明天早上或者下午才回去。”
钟煦呈下意识地顺着他的话看向了窗外。
大雨滂沱,乌云密布,天气看上去非常不好。
“是因为下雨不方便走吗?”钟煦呈没来由地有些担心,“要不要我去接你?”
接到报案的片儿警已经朝医院来了,庭钺看着外头由远及近的身影,尽管诸多不舍,还是轻声拒绝了:“不用,一点小事而已,我自己能解决。”
“那好吧,”钟煦呈温声叮嘱:“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
将手机收回兜里,庭钺稍稍站直。
陈根的情况要比他儿子好一些,躺在走廊的病床上,一见到警察就哀声嚎叫:“警察同志,就是他打的我,你一定把他抓起来,我要告他!哎呦,护士,我的骨头是不是断了,好疼啊”
被陈根扒拉着的护士十分不耐烦,她是住在陈根家附近的,这人渣天天打儿子的动静左邻右舍都能听见,要不是职责所在,她根本就不想替这种人上药。
“喊喊喊,喊什么,你儿子可比你严重多了,”护士把衣服拽回来,动作粗鲁地替陈根缠好纱布,“你的手没断,骨头也没事,不要再大喊大叫吵到其他病人了。”
片儿警对陈根不陌生,这人因为喝多了失手杀了自己老婆,坐了七年牢,一个月前才放出来。
对于这种泼皮无赖说的话,片儿警向来都是只听三分,他把目光投向站在一旁的庭钺,率先向他了解情况:“先生,你们是因为什么才起的争执?”
庭钺脸上有道淡淡的血痕,不难看出是被利器刮伤的,他皮肤白,加上面相斯文漂亮,比起前科累累的陈根,显然更像个无辜的受害者。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疾不徐,避重就轻地陈述事实:“我路过他家门口,看到他在打孩子。”
“那孩子一动不动倒在地上,我以为他把孩子打死了,一时心急,所以闯进去想把他拉开,没想到他发了疯似的拿着酒瓶往我身上戳,出于自卫我才打伤了他。”
陈根本来还想反咬一口讹点钱,见庭钺不慌不忙,顿时坐不住地插话:“他撒谎!我没打孩子!是我儿子自己闲不住跑出去摔了一跤,然后这人就冲出来”
他话还没说完,帮他包扎的护士就听不下去了:“你儿子后脑勺的伤很明显是外物击打所致,再偏一点就会伤到神经,轻则失明瘫痪,重则没命,你别胡扯了!”
与此同时,白永嘉带着一个人过来了。
是先前站在墙根和陈根对骂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名叫陈军,祖上三代和陈根有些亲戚关系,和陈根做了十几年邻居,看着他打完老婆又打孩子,曾经好心去劝过架,没想到陈根嘴里不干不净诬陷自己跟他老婆有一腿。
陈军为了避嫌没敢再管他们的家事,白永嘉报警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跟过来看看情况。
老子不是东西,但小的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