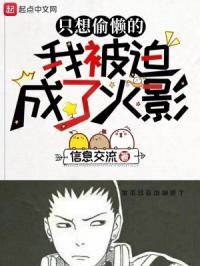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走出绝境的秘诀有什么感受和启示 > 第36頁(第1页)
第36頁(第1页)
后街男孩翻了兩面,又灌了七八瓶啤酒的林巍終於容量不夠了,步伐不穩地起身上趟廁所,回來往懶人沙發坐的時候力道重得好像是摔進去,弄出咕咚一聲響來。
秦大沛剛要看他,樓下那一撥人的動靜重大了起來,秦大沛蹙了眉頭罵人,「我下去把這幫兒子趕走。冬陽你瞅著點兒你林哥。」
秦冬陽嗯了一聲,眼瞅著林巍已經進入半睡狀態,連忙去把房頂通風用的小窗戶拉下來關嚴實,而後拽過一張空調毯來,要給林巍蓋上。
林巍穿著上班時的襯衫,挺括布料裹著特沒姿態的身體,應該很不舒服,皺著眉頭蹭了一蹭。可能是因酒重,剛剛上完廁所的人沒把自己整理利索,褲扣沒扣,拉鏈也沒拉,隨隨便便扎了腰帶就撲回來。
秦冬陽輕手輕腳地將空調被蓋到他的身上,眼睛隨意瞥了一下就注意到他裂開來的褲閘,似乎有抹內褲輪廓和些許硬邦邦的腹肌不由分說地闖進視線里來。
沒露關鍵部位,都是成年男人,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可那刺激對於秦冬陽來說過於強烈,大出預料全無準備,某些東西突然之間排山倒海般地從他身體裡面呼嘯而過,摧枯拉朽地匯集一處,直奔重要器官。
禿嚕一下,他就硬了。
因為蓋被那個姿勢,秦冬陽的身體距離林巍也就一拳不到,突如其來的雄起幾乎抵到了林巍的身體,他被自己嚇了老大老大一跳,駭然地朝下看看,然後滿臉驚詫地抬眼瞧瞧近在咫尺的林巍,猛然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動作非常激烈地蹦開去,背轉了身拼命喘氣。
這是怎麼了?
這是幹什麼?
自己怎麼如此齷齪?
躺在那兒的是林哥啊!
第21章心硬如鐵
周身的血全都凝滯掉了,任憑軀體極力催動,極力想要迅恢復,就是不肯正常循環。
秦冬陽手腳冰涼動彈不得,只有那個地方還在熾熱還在固執己見地沒羞沒臊。
不知過了多久,樓梯上又傳來腳步聲,神魂離竅的秦冬陽驟然之間元魂歸位,飛轉回了身,動作極快地把林巍身上的空調毯往下拉了一下,而後摔進另外一處沙發裡面閉眼裝睡。
裝也要把無恥藏住,絕對不能露餡,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自己存了這麼骯髒的心。
秦大沛大步走上三樓,看見兩人都睡著了,好氣而又好笑地罵了一句,「都他媽的挺好養活嘿!」
他先過去摸摸林巍的臉,查看他的情況,林巍皺著眉頭閃開那手,翻了翻身,繼續睡去。
秦大沛便又走到弟弟身邊,拿腳踢踢幾乎趴進沙發里的人兒,「秦冬陽,起來!別睡在這兒,哥送你回家。」
秦冬陽如同睡死了去,無論如何不肯應聲。
秦大沛見狀又低聲罵,「你是不是也跟著喝紅酒了?小傻玩意兒,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那就在這兒窩著,難受死你!」
秦冬陽果然難受死了,他恨不得自己真的喝過紅酒,那樣就有抵賴,可以把錯歸結為酒。
這個秘密被他死死守了好多年,從不與人透露,也肯不認真回想,仿佛一切就是似假非真的夢,就是糊裡糊塗中的妄自蠢動,並非現實。
沒想到卻被盛怒里的林巍毫不留情地撕碎了他的自我欺騙,秦冬陽無可抵擋地跌入不願相信同時也無法面對無法承受的冰窟裡面,被那徹骨的冷和迅扎進內里的寒氣之刀合力殺明白了——原來當日裝睡的人並不只有自己,原來他努力扮了這麼多年的單純竟是一場笑話。
那個惹得自己看清自己的心,那個讓小弟弟秦冬陽明白他竟對一個哥哥產生了興的林巍其實早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卻始終冷眼旁觀,無動於衷地瞧著他是如何竭盡全力地保持分寸的。
這會兒還要用如此譏嘲的語氣撕開那被拼力壓在歲月深處的秘密。
為什麼如此狠?
但有一點兒慈悲,也不會在這種關頭拆穿。
揮過刀劍,林巍沸騰的暴虐欲稍稍緩解了些,盯著被凍成冰雕似的秦冬陽看了一會兒。
等不到這個人自己恢復知覺,林巍的耐性很快又耗盡了,使勁兒抓過秦冬陽擺在門邊的鞋,開門一丟,同時抬手搡人,把那泥塑般的傢伙使勁兒推到外面,再吼了聲,「滾!」
他也有些不願面對這種情況,堅持強硬也是一種解救之道。
廊道空曠,那個「滾」字嗡然發出一段尾音,還未消散,房門就已咣當關合,毫不留情地把根本無法自如行動的秦冬陽擋在光線昏暗的樓梯間裡。
體表那層冰殼被推裂了,手腳僵直的秦冬陽承受不住身體深處傳出來的劇痛,緩緩蹲了下去,為不至於癱倒,手掌死死按住地面。
恰巧有個住戶由上而下,路過赤腳蜷縮著的秦冬陽身邊,非常納悶地看看這個使勁兒勾著腦袋的年輕男人,又看看被甩出去老遠的鞋,心想瞧著還挺精緻的人,怎麼混成這副慘狀?爹媽沒有狠心做到這地步吧?那是女朋友?什麼厲害女人能把一個青春正好的小伙子逼得如此可憐?
唉!造孽!
門裡面的林巍也僵立著,野蠻無情和心狠手辣並沒能夠安撫他的痛苦,反而激出懊悔之心。
如果沒有鬼使神差地往沈浩澄的辦公室門口走那幾步,他就不會看到不想看的場面,也就不會沒理智地配合林北得安排好的相親,不會傷害到無辜的彭商商,不會對始終謹小慎微的秦冬陽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