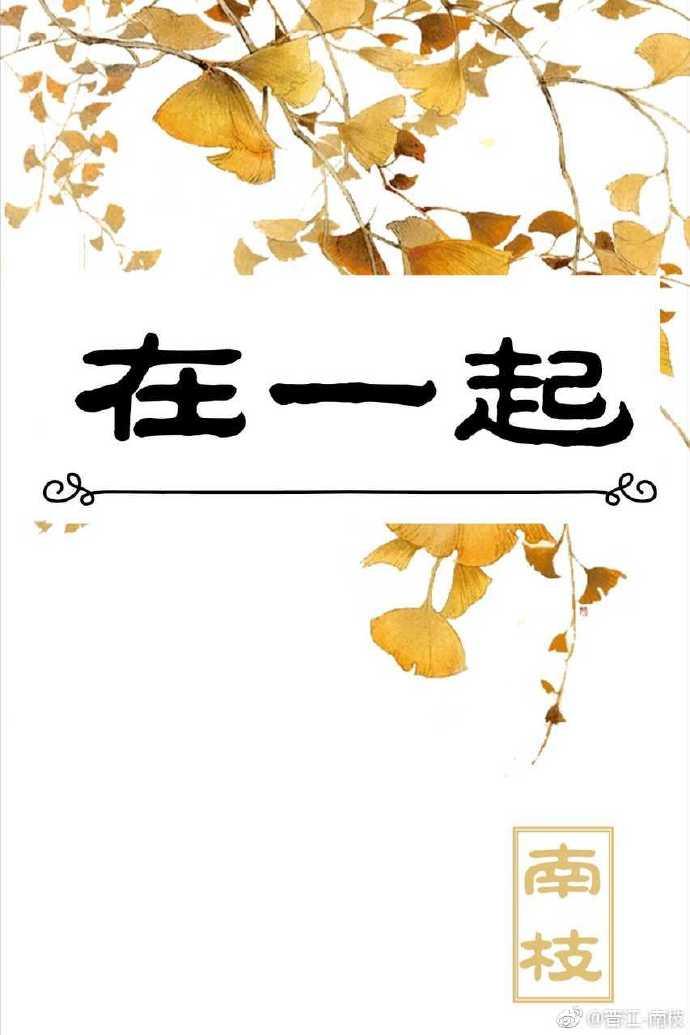UPU小说网>哑雀无声成语 > 第22章(第1页)
第22章(第1页)
大脑嗡嗡,还有点想吐。
倪雀一时根本爬不起来。
旁边滚着那截倪保昌刚才用来砸她的实心木头,倪雀伸过手去,将木头拨远。
倪保昌已经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二话不说抓起她的头发,拽着她往羊圈的方向走。
“臭婊子,贱东西,我看你还怎么跑?!”
“来,你来给老子数数,数数这里有几头羊,我看看我刚才是不是数错了。”
“要是没数错,羊真的丢了,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头皮被头发拉扯着,仿佛要从颅顶剥落,倪雀疼得眼泪直往下流,她痛得“啊啊啊”地尖叫着,示弱地喊“爸爸”,希望倪保昌能善心大发地松开拽她头发的手。
倪保昌无动于衷,倪雀被他粗暴地拖拽着,后背与地面摩擦,衣服的布料被碎石持续地磨烂。
太疼了。
倪雀受不了。
她抬手也去拽自己的头发,和倪保昌形成一个相左的力。同时,她的脚也在地上拼命地蹬着,这给倪保昌的拖行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倪保昌骂了一句,松开手,改去拽她的胳膊。
头发得到解放,倪雀冒了一身的虚汗,几近脱力。
倪保昌就这么拖麻袋似的把她拖到了羊圈门口,然后撒手,指着羊圈的门:“我回来的时候,锁就是这么挂着的,没扣死,打开一看,里头少了两只羊。”
他踹了倪雀一脚:“滚过去,给我数一遍。”
倪雀颤抖着说:“我锁了门的。”
倪保昌一字一顿:“给、我、数。”
倪雀忍着头昏眼花,忍着腰背剧痛,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离羊圈的门只有两步的距离,但她走得极其拖沓磨蹭。
如果真如倪保昌所说,丢了两只羊,那么这扇门一旦被打开,于她而言,如地狱之门被打开没什么两样。
那些羊对倪保昌来说,就是没钱花时候的钱袋子,丢了会要他命。
而他会要倪雀的命。
手碰上门锁的时候,倪雀在心里祈祷,一定是倪保昌喝多了眼花数错了,八只羊都好好地在里面待着。
但她又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小太小了。
如果不是倪保昌看见羊圈的门锁有异样,他是不会特意过来查看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倪保昌从不会把羊圈的门的钥匙带在身上。
现在锁开着,最大概率就是真的着贼了。
倪雀终究是拿下锁打开了门。
羊圈不大,一眼望尽。
只有六只,两只最肥、ee不见了踪影。
倪雀的心一下跌至谷底,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出卖了她。
倪保昌立马从她的脸上读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