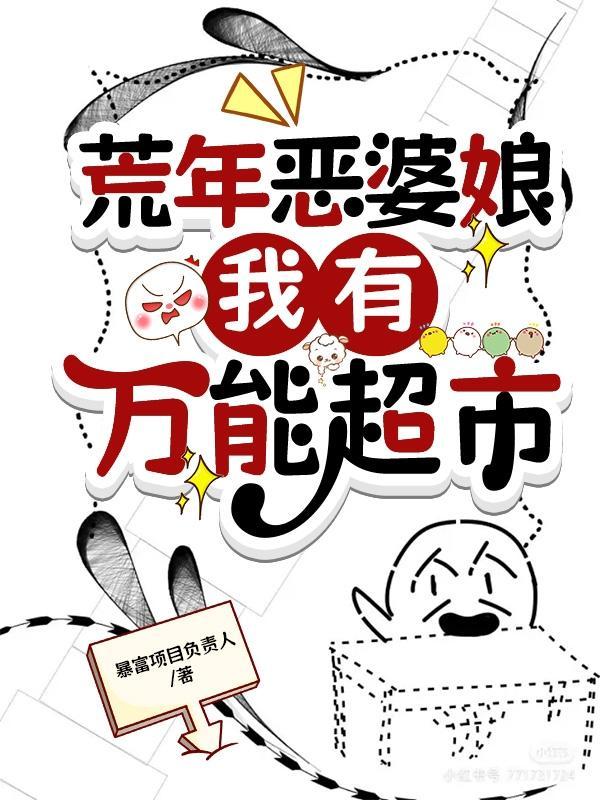UPU小说网>破碎后劲第几章带球跑 > 第11章(第3页)
第11章(第3页)
岑谙抬高手臂将乌林晚拉开的床帘扯上,回自己的位置打开台灯,灯光扫亮屋里大半空间,他才察觉寝室空了很多:“他俩这么快就走了?”
“啊,本地人嘛,吃过晚饭收拾收拾就走人了。”乌林晚攥着堆纸巾球爬下来,扔垃圾桶后扎上袋口,“我就是好几天没直播了,皮痒。”
这人越解释越惹人笑,岑谙小口喝着牛奶,弯弯眼睛“嗯”了声。
乌林晚登时炸了:“你笑什么!”
“哪有人播成你那样儿的。”岑谙说,“你俩都进展到这种关系了?”
结果乌林晚否认了:“没有啊,他还在追我。”
岑谙惊异道:“那你刚才是在搞什么?”
乌林晚夺下岑谙的牛奶猛喝一口:“给他点反馈€€€€啊靠,这牛奶冷得,你怎么喝得下去的?”
岑谙只觉自己被打破了对感情展的认知,他问:“那你之后会答应他吗?”
“会吧。”乌林晚毋庸置疑道,“你不知道,当识破他开小号给我刷快艇,又装着长辈口吻在弹幕建议我唱歌跳舞不如裹好衣服教微观经济,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也太可爱了。”
岑谙还想确认些什么:“这会儿不担心他就图你在他情时给他打抑制剂了?”
“不啊,”乌林晚笑了起来,“他说他仅仅是抱着我就会很舒服。”
岑谙脑海里浮现应筵嫌他吵,又吼他赶紧扎针的那一幕,不知怎的就笑不出来了。
今晚出了很多汗,他弯身扎在衣柜里翻衣服,打算洗完澡就好好睡一觉,但只开了盏台灯的寝室太暗了,柜子里塞的东西也太多了,他感觉所有衣物在他眼里都一个色,所有布料摸在手里都是冰凉的触感。
乌林晚短暂的害羞过后又恢复了咋咋呼呼的面孔,在他身后喋喋不休道:“小宝你别喝那个牛奶了,放凉了都,大冷天喝了要拉肚子。”
“哎我说啊,原本今晚我要跟师弟去你兼职那俱乐部的,然后师弟跟我说那里今晚不开放预约。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岑谙抓着一件羽绒服的袖子,弯身久了腰疼,他慢慢地、慢慢地蹲下来,脑袋依然埋在衣服堆里。
乌林晚说:“对了你看班群了吗,学校真是闲得蛋疼……你要找房子的话跟我说一声吧,我陪你。”
岑谙这时候才后知后觉,他晚上独自窝在小包间的卫生间时压根没把眼泪擦干透彻,因为那些滚烫的液体又不听使唤地从眼眶里涌出来,还好光线暗淡,身后人不会现他蹭在衣服上的湿痕。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似乎这样才能确信自己没有缺氧:“好……”
那张合影最终被岑谙设置成了气象软件的背景,每天早上查看天气的时候就能看见,又不会像屏保或聊天背景那般容易被人现。
气象软件是岑谙找了很久才找出来能设置自定义背景的,唯一缺点就是偶尔有扰人的广告弹窗,不过不影响使用。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在所有人都眉飞色舞计划着怎么度过跨年夜的时候,岑谙叫了个车子,拉上他的箱子和两大包行李,从学校寝室楼搬到了他的新家。
给这个小屋子安上“新”字属实有点抬价€€€€屋子隐匿在旧城区一排老商铺的背面,明明路狭窄得连轿车都无法开进去,偏要起个具有欺骗性的名字,叫“瀛村大街”。
这里的房屋挨得尤其紧密,电线爬遍墙体,汩汩漏水的铁锈水管周边长满青苔。
岑谙住在其中一个三层楼房的顶层,一房一卫,连客厅和阳台都没有,胜在租金便宜,一个月包水电才八百五。
搞完卫生安置好行李,岑谙冲了个澡,头半干不干就倒在只铺了张棉被没有松软床垫的床上,目光定在只开了个缝的窗户外。
很远很远的地方是林立的高楼,而在那些影影绰绰的建筑之间,岑谙居然能看见月亮。
他居然能在这么狭小而破旧的屋子里,那么清楚地感受到月光,或许明天一醒来也能摸到暖阳。
放假的日子,岑谙白天就窝在家里温书刷题,晚上去俱乐部兼职,之前找他玩盲品的那个a1pha后来又来了一次,不过没喊他坐下来玩了,只跟他探讨了下酒文化。
岑谙对此颇感庆幸,自从上回沙龙莫名其妙的呕吐,他现在都不大敢碰酒,还好店里的客人没什么陪酒的需求。
应筵不常来俱乐部,两人见面次数不多,通常都是在手机里不咸不淡地聊上几句,岑谙问他吃了吗,应筵回个“嗯”,岑谙又问他最近忙什么,应筵说给一本生活美学杂志撰稿,写一篇关于葡萄酒文化的科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