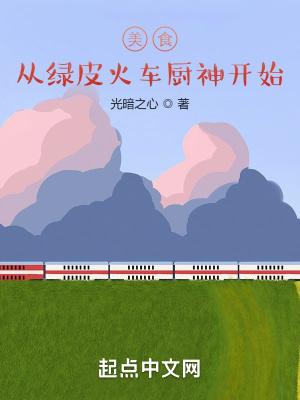UPU小说网>士兵突击袁许深海番外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唐梓欣有些心不在焉,她揽着表弟的胳膊,只盯着地面,袁朗仿佛也像是在想些什么,没注意到这一切。
“是。”丝毫没察觉的冯理舒了口气,这样最好,免得大家都不自在。
“你跟我过来,冯理。”面色冷淡的唐梓欣用了点力气拉冯理,“我有点话想跟你说。”
姐弟俩离开了,剩一个袁朗从大厅走出来,他想许三多,却并不想见他,医院里不让抽烟,人就挪到墙根处蹲着点火,烟灰落到湿润的泥土里,被他用鞋底磨平。
没人在场,袁朗脸上没有表情,一根接一根的抽,就这样放空了很久。
庄安安听说许三多要走,脸上掩不住的失落,虽然只跟许三多认识了两天,但两人已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至少她是这么想的),没成想许三多说走就走,这一去就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正如许三多所说的:“天南海北,去哪都呆不长久。”
她自觉是送走一只候鸟,不可避免地有了伤感,两人交换了地址,看着彼此都很不舍。许三多人生中第一次和女孩说这么多话,又和她交了朋友,飘浮的女性形象在他心里一下子落了地,变得亲切和可爱,再不是惹人困惑和害怕的模样。
两个人没来得及依依送别,就有人来通知庄安安准备一场手术,临别时,她边走,边回头嘱咐许三多安置后给她写信,最后她喊“再见”。
许三多不顾医院清净,也喊“再见”“再见”。
等庄安安的身影消失不见,许三多站了一会儿,转身收拾行李,说是行李,不过就是几件军装,他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常言说穿什么衣服想什么事,换上军装后,他又想起充满挑战的军旅生活。
收拾完备,正好赶上来接他的齐桓,齐桓拍了把他的脑袋,替他接过行李,爽朗地说:“走了走了,队长和南瓜们正等咱们呢。”
齐桓这样子想让许三多调皮一下:“收成怎么样?”
“大丰收!”齐桓哈哈大笑,“对了,还有那个冯理,一会儿就能看见他。”
俩人走到门口,那停了两辆车,都是许三多熟悉的牌照,车前站着的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听到声音后齐刷刷看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许三多曾经俘虏过的冯理。
陈水生和马大路好奇地望着许三多,从冯理嘴里听过许三多事迹的陈水生更是如此,眼睛溜溜地绕着许三多转,也没看出什么出奇的。
他拍拍冯理,没有回声,他回头一看,倒让他有点惊讶。
出乎他意料的是,冯理脸上既没有仇人见面的分外眼红,也没有夙愿得偿的欣喜,反而把头侧到一边,仿佛忍耐着什么。
怎么了这是,之前不是还许三多长许三多短的吗?
他没放在心上,因为袁朗带着一身烟味走过来,点了点人数,最后拍拍车身:“我们走吧,同志们?”
许三多问:“队长,楚中校他们是不是……”
“是。”袁朗知道他想说什么:“怎么,你想见他们?”
彼此不熟,见面也没什么话可说的,许三多摇了摇头。
齐桓开车带着仨南瓜,袁朗对许三多指了指剩下那辆车,自己拿了车钥匙就要上主驾,许三多拦在他前面说我来开车,被袁朗拒绝,说上车。
他语气平平,却不容分说,许三多再没说什么,坐上副驾驶,系好安全带。
袁朗松开离合,车像离弦的箭般冲出去,许三多身体撞到椅背上,吃惊地望着他的侧脸。
袁朗问:“还生我气吗?”
“生气?”许三多都快把这事忘了,严格来讲,他不算生气,只是一些微妙的小情绪,但他没解释,“没有了。”
他看见自己的队长勾了嘴角,却不像愉快的样子。
“那个姑娘,叫庄安安的,你跟她怎么认识的?”
许三多就把来龙去脉说了,那女孩很活泼,却和外表不相符的细心,在医院的两天很关照她,而且她很勇敢,第一次面对流血就扛了过去,很棒的女孩。
他讲完,袁朗就笑:“一个护士还怕拿手术刀,能叫合格吗?”
“一个兵怕拿枪,队长,要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合格,但是我觉得她比我要勇敢,她克服了,真的。”许三多忍不住想要替庄安安说话。
袁朗压下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三多……”说着他用一种很诚恳的目光望向许三多,“你要为一个刚没认识两天的女孩跟我急吗?”
许三多心里总有点酸,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羞愧吧,情不自禁疏远一个关照自己的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成长了,这是不是像连长说的“耍小性儿”呢。
队长这么问,他应该说“不是”,可酝酿了一下,可这话终究说不出口。
把许三多的神色收入眼里,袁朗想,许三多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心啊。
“你嫂子说,早晚有一天,我得放手。”袁朗想着,竟也说了出来,“让我怎么放得下心。”
“嫂子说的对,您也不能照顾我一辈子呀。”许三多把自己这两天想的慢慢说了出来,“等有一天,也轮到我去照顾别人了。”
说完后,他便侧头去看窗外飞驰的树木。
看着许三多沉静的侧脸,有那么一刹那,袁朗几乎想要脱口而出“那我照顾你一辈子”,可那不合适,也不现实,他终究没有说出口。
如果当初说出来,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偶尔,袁朗会这样想,可这设想终究是没有依据,因为正在望着远方的许三多,已经默认将会在属于他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切将以告别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