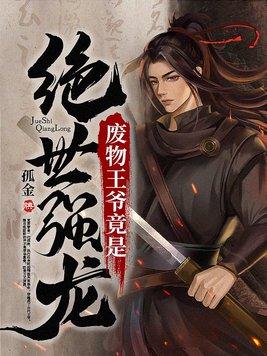UPU小说网>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竹马txt > 第73頁(第2页)
第73頁(第2页)
但如果忽略溫度,單是憑肉眼看,根本看不出這房子許久未住人。
家具一應俱全,空氣里能嗅見淡淡的清潔香氛,所過之處皆無粉塵。
儼然是有人日常在打理。
江元洲借著落進屋那點月色,緩慢往二樓走去。
葉懷騁終於忍不住了,壓低聲音:「你到底想幹什麼?」
江元洲沒理他,拐上二樓,走到江和雅過去住的房間門口停下。
葉懷騁還停在一樓。
他已經看不見身影沒入二樓的江元洲,但他清楚,他現在也絕不可能走掉。
只要他現在踏出這棟房子一步,車裡的那兩個保鏢一定會馬上下車,攔住他去路。
江元洲從始至終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對他的行動進行強制性左右。
可也明擺著,只往他面前擺了一條路——跟上江元洲,走進江元洲為他設下的局裡。
葉懷騁已經很多年沒有體會過這種明知被人牽著鼻子走,卻還是必須捏著鼻子跟他走的憋屈感受了。
一時間記憶翻湧,這孩子經年裡曾數不清多少次帶給他的恐懼和憋悶又重漫上心頭。
葉懷騁咬緊牙關,強行將那些令他自尊受損的情緒壓制下去。
毛頭小子終歸是毛頭小子,能翻出什麼大浪。
他壓下眉,終於邁開腿,往二樓走去。
江元洲等在江和雅房間門口沒進屋。
等葉懷騁走近了,他才推開房門,緩緩走入。
仍是沒開燈。
屋內窗簾沒拉。
窗外半是海市夜色下寂靜翻湧的海,半是遠處星星點點的煙火人家。
月色將室內物件籠罩在一片模糊下。
模糊中,床前擺了張椅子。
江元洲在葉懷騁的注視下,邁開腿,踩上椅子,而後轉身,眸中不帶任何感情地低頭朝葉懷騁看去。
那一瞬,那張與江和雅七八分像的臉在月色模糊下,讓葉懷騁好像回到了三年前。
警察將死亡現場的照片拍在他面前,厲聲問他:「葉懷騁,2o2o年6月15日下午三點,你在什麼地方?」
照片裡的女人被一根麻繩懸於房梁之上。
面色灰白,眼睛卻還睜著。
葉懷騁渾身止不住戰慄,但還是強行對上江元洲視線,故作鎮定地嗤笑道:「小洲,三年沒見,你怎麼變蠢了?千辛萬苦帶我來這裡,就為了擺這齣嚇我?」
「警察給出的死亡時間是下午三點,我早上十點就離開了,下午三點也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
他越說越覺得自己占據回了上風,語氣也逐漸變得輕快:「三年了,你還沒清醒過來嗎?你媽她,就是自己發病,想不開,上吊自殺的。」
他說著,眼神忽然變得戲謔:「這你應該最清楚啊!她發起病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不是嗎?她不是甚至曾經差點,把你掐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