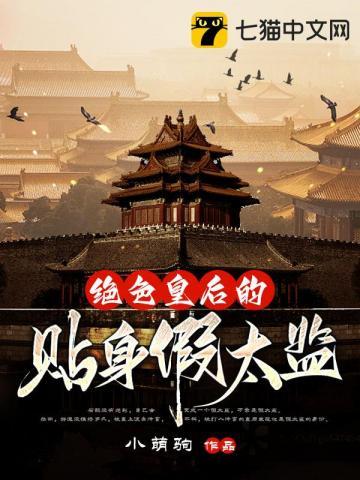UPU小说网>温柔刀梦筱二 > 第106章(第1页)
第106章(第1页)
打完出门,她被门槛绊了一下。骨折就是这么来的。
李菜来的时候,家里人连带医生都在劝奶奶,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不要总是这个脾气,万一惹上麻烦就不好了。
李菜检查了一下东西,发现他们的床位没有尿壶。奶奶的情况肯定下不了地,她去找了护士。
病人总是需要看护,大家分批次去吃晚饭。轮到李菜他们一家,刚下楼,李菜她妈就对着李菜她爸义愤填膺:“亏他们说得出口!他们要上班,我们去伺候妈。哦,那我们该的,妈不是他们的妈,他们不做事,我们必须受累?还说李菜离这里近方便,那玲玲还不用上班嘞,怎么不叫玲玲来……”
大人说话,李菜不插嘴。
大伯伯向来精明,陪护这种事,就算不想干,第一天还是要做做样子。毕竟是自己亲妈。
李菜她妈怎会看不透,也拽着李菜她爸留下了。病房里突然多了这么多人,害得隔壁床的病人都犯嘀咕。
大半夜,李菜的奶奶鼾声震天。陪护的人都坐着,也没睡好。
李菜站在走廊上。
医院是充满分别的地方。
夜里也不熄灭灯光的护士站,屏幕上鲜红的数字,消毒水的气味,一模一样的房间门。
到处都是白色。对她来说,这种环境是一种暴力,无时不刻令她想起那个夜晚。爸爸在玩手机,妈妈趴着睡着了,李菜可以和他们说,但是,却又不知道这样说才好。
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她的痛苦太过纤细了,而且太过具体。李菜只能安慰自己,今天已经跨过了一道槛。
快到早晨,这个星期指标都完成了,李菜和老板请了一天假,去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洗漱。那里有扇窗户。
她想打开它,但用力也只有一条缝隙。
安全考虑,医院有规定,每一扇窗户要么封死,要么就只能打开一部分。风吹不进来。
回到病房,其他人也起来了。留下李菜她爸陪护,其他人出去吃早饭,顺便到银行取钱。李菜想了一下,还要给奶奶买一个夜壶。奶奶用不惯医院那个。楼下商店就有。
李菜和亲戚们一起下楼,本来想从住院部出去,但门还没开,所以转到门诊部的前门。这样一折腾,天就大亮了。天气不错,还是个艳阳天。
他们说着话往外走。李菜说应该吃完饭再去买尿壶。大妈开了个恶心玩笑,又拿自己出门着急,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自嘲。一家人都在笑,其乐融融,一派和谐。李菜也笑。
太阳底下,李耀祖站在医院门口。
这里和其他场所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人和外面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走进去这件事很困难,待在里面也很煎熬。消毒水的味道是毒气,白色是刀尖,这里是无形的焚烧炉,能轻易把他们杀死。
眼球酸涩,耳鸣轰隆,身上能患职业病的地方都在痛,超过了生理范畴,随时随地提醒他,他始终抱着胸口被针刺过的孩子。李耀祖不是能安安心心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也没有资格幸福地生活。
可是,确认完医院,他立刻冲进来,没有犹豫。李耀祖拿着手机,贴在耳边。四目相对时,李菜的笑容还没散去。
他叫了她的名字:“李菜!”
李菜说:“啊?!”
见面后,李耀祖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她,从头到脚,里里外外:“你干什么?摔了?撞到哪里了?你干嘛不接电话?”
“啊?”
“你——”李耀祖看到了她身后张大嘴瞪大眼的七大姑八大姨。
她的视线扫过他。
李耀祖的衣服皱巴巴的,应该落下了外套,手臂上有灰白色的痕迹,不知道是在哪撞到的墙,只有看电脑时才会戴的眼镜没有摘。晚上没有高铁通行,只能坐火车,假如要临时买票,大概率是无座的站票。
她重新看向他的眼镜,在亲戚或体贴或好奇的目光中打了声招呼,推着他旁边走。
李菜说:“我把你拉黑了。”
李菜继续说:“不是我骨折。”
李菜最后说:“你来了。”
几个月前,李菜问李耀祖“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连一桶水都无法提上楼的李耀祖没回答。
他不看她的眼睛,于是她明白了。
李菜说“我知道了”,转身一个人上楼。李菜很少生气,但那一天,她又发火了。
冰箱里囤了半年的食材,她决定快速消灭。李菜做冰面包,打发奶油没用机器,自己靠手搅,搅得锅底刷刷响。
值得一提,靠怒火做出来的面包很好吃。谁没吃到谁吃亏。
医院大厅人来人往,李耀祖看着她,表情像定格了。片刻,他抬起左边的手,盖住眼睛。一整夜没睡,那里一片滚烫。手掌缓慢移动,逐渐按住额头。
“嗯。”他说。
作者有话说:
弹跳的银
一家人在医院旁的早餐店碰面。李菜的妈妈、大伯和大妈提前去,李耀祖和李菜随后才到。
店门口烧着热腾腾的一锅水,桌子摆到人行道上来。一大清早,来往的也都是住在附近的人,习惯了这样的日常,不会有怨言。
李菜的妈妈、大伯和大妈三个中年人各自心怀鬼胎。大伯伯在敲筷子,大妈在用手机问大女儿什么时候过来。李菜她妈想发消息给李菜,怕李菜不看,又还是发给李菜她爸,问的是病房里还有水果没有,赶紧去买一点,挑贵的买。
李菜在讲什么,李耀祖冷着脸,低头在听她说。两个人没有勾着手,也没有更亲密的动作。走进店里,他们的亮相很怪。李耀祖拎着新买的尿壶,李菜走在他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