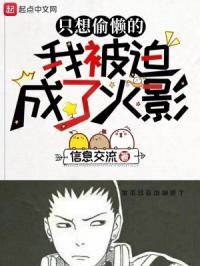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小夫郎破产了晋江 > 第7頁(第2页)
第7頁(第2页)
季子漠是個很好的合作夥伴,自己翻箱倒櫃的找了被褥,在床邊打了地鋪,躺著沉沉睡去。
臨睡前還和齊玉道了聲晚安。
門外又飄起了雪,齊玉推開門,進屋的冷風讓睡著的季子漠縮了縮身子。
雪中的喜服,太過怪異,他合上門,不知自己應該去何處。
屬於他的房間,現在睡著另一個人,那個人,原應當是他的夫君。
司琴揉著眼,從一旁的耳房出來,見那雪中獨自矗立的身影,一時有些想哭。
她拽著齊玉往廊下走,給他拍打著肩上的雪。
又把繡著金絲祥雲的白色披風披在他身上。
帶著哭腔問:「少爺,是姑爺不好嗎?」
咱們能不能不想鄭少爺了。
司琴原以為他不會回答,誰料齊玉苦笑道:「嗯,很不好。」
什麼神童,才學再高,也是一個混帳。
季子漠穿過來後,睡的都是硬床板,只鋪了一層硬被,天天隔得身體疼,睡覺跟上刑一般。
昨日他在齊玉房中翻出兩床嶄的厚被,一床鋪一床蓋,暄軟的一夜好夢。
敲敲打打聲擾人清夢,忍無可忍的睜開眼,就見一丫鬟拿著雞毛撣子,左敲敲,右打打,桌椅拉來拉去。
「你們家都是大清早的打掃衛生?」
醒都醒了,季子漠轉到地鋪一側坐著,自己穿靴子。
隨口一問卻無人回答,他又看過去:「聽不到我說話?你叫什麼名字?」
繼續無人答。
他把房間環顧:「齊玉呢?出門這麼早,今天不是要帶我給爹娘敬茶的嗎?他不陪我一起嗎?」
和齊玉話少相反,季子漠吃好穿好住好,心情好的情況下,話是多的不能再多。
再加上無手機等電子產品,不說話怕是要無聊死了。
「姑爺,你與少爺已經成婚,怎麼可以直接喊他的名字。」
敲敲打打的小姑娘,突然變成了炸毛的貓兒,氣憤的瞪著季子漠。
季子漠保持著穿鞋的動作,不解的轉頭過去:「不叫齊玉叫什麼?玉兒?小玉?玉玉?齊齊?小齊?齊兒?」
「都不行?那總不能是寶玉吧?」季子漠試探著猜出最後一個名字,寶玉肯定不行,這個名字太出名,他對著齊玉定是叫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