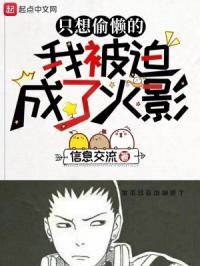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被太子娇宠的日常第四十章完整版 > 第49章 把人拉下了神坛(第2页)
第49章 把人拉下了神坛(第2页)
如花花没当回事。钟离廷却微微蹙眉。
这会都已经开始流鼻血了,很难说药性如果不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转身,钟离廷烦躁的朝外喝了一声,道:“来人啊,军医怎么还没来?”
“来了来了!”
作为军医所里唯一还年轻点儿的军医,这人被卫令催命般催了一番,路上一路小跑,连口气都没敢喘,马不停蹄的赶了过来。这刚到门口,就听到少将军喊人,便立马应了声。
钟离廷身上没穿披风,他抬手解了锦衣外袍兜头丢给如花花,才沉声道,“进来。”
军医喘着气走进帐篷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副这样的场景。
他们少将军未着外衫,一身单薄白色中衣,髻微散。
如花花赤着一双小脚站在长毯上,身上严严实实的裹着着一件过长的,并不属于她自己的锦袍,一截白嫩的脚趾踩在垂下的一截衣摆上,露出了一点偏粉的指甲。
细看下,小姑娘眼角还挂着些泪痕,睫毛忽颤忽颤的,面颊透着些病态的红,整个人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可怜与委屈。
他们少将军这是……那兽什么……大了吗?
军医瞪大了眼,不由喘了口粗气,他仿佛窥探到了什么天机一般,匆匆埋下头,吞吞吐吐的开口唤,“少……少将军……”
钟离廷不冷不热的嗯了一声,顿了顿,再开口时,脸色微透着些不自在,“春不晚……可有解?”
春不晚?
那不是皇城里广为流传的一种闺房秘药吗?据说后劲极大的那种?
军医一惊,艰难咽了口口水,嘴皮动了动,口中斟酌着词句,遣词造句半天,小心翼翼的道,“……就,就是春……春风一度……可解……”
军医紧张的差点嘴瓢。
“废话!”钟离廷脸色一黑。
要这种解他还用让人喊军医?
军医默默更住,脚趾忍不住扣地。
他当然也知道这是废话啊。
可就是说,都是男人,这种一目了然就有答案的事干嘛还叫他来啊!
“我叫你来不是听这些废话的!”钟离廷声音冷沉,“你可……”
本就精神紧绷的军医一听这话,神经一下子断了,心道怪不得卫少将军专挑年轻的军医叫,原来还有这层意思。
军医白着一张脸,哐的一下跪了下来,吭吭哧哧的往外吐字,“卑……卑职不可……卑职无用……少将军您,您还是继、继续……”
“闭嘴!”钟离廷脸色一沉,“我是问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法子?”
这样子啊……
军医脸色这才逐渐放缓,抬袖擦了擦鬓角的汗,努力的开始思考。
被忽略的如花花皱着一张小脸,忍不住掀了掀身上牢牢裹着的外袍,口中迷迷糊糊的嘟囔着,“好热啊……哥哥……”
“不可以脱。”钟离廷一把将那外袍按了回去,抓着领口不让她把衣裳脱下来。
如花花委屈的抠着她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