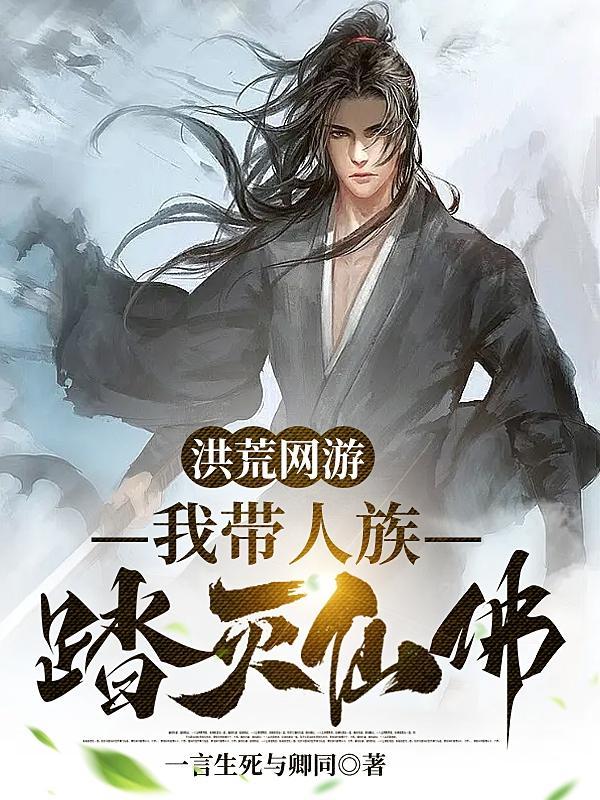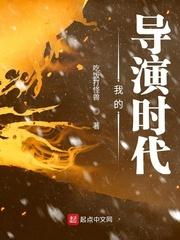UPU小说网>女经理14p > 第121章 在国内工作的外国同事们(第3页)
第121章 在国内工作的外国同事们(第3页)
“啊,怎么回事!”
“在酒吧里面和别人争风吃醋呗,把人打了头破了。人家以为外国人有钱,想敲多点。我一直说菲利宾人,没啥钱,不相信,扯了好久。”
“那他没什么表示吗?”
“他喝多了,刚开始不是很清醒,还总来横的。后来清醒了,才软了下来。我问了几个朋友,定了个价钱。他真是吃光用光,没几个钱,还是小芳垫的钱。”
“他今天怎么不来上班?”
“也挂了彩,也有点不好意思吧。说请几天假。”
过了几天,中年菲利宾同事终于来上班了,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颓废了很多,也安静下来,不再说和工作无关的事情了。一个多月后,他消失了。我才知道就在那事生不久,他就和工程部经理直接提了离职,听说回菲利宾去了。
(三)拖家带口的印度朋友
甲骨文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条业务线刚在深圳开展业务时,都会派一些经验丰富的外国同事过来帮助深圳同事们快熟悉业务。大部分都是资深的工程师,偶尔也会是老板直接过来。
而我在甲骨文工作的十一年里,打交道的大部分都是印度同事。由于大部分印度人都是印度教徒,不吃荤腥,加上我们物价高,在中国短期出差都叫苦连天,更别说常驻了。所以我们组很少有像其他组的外国同事来国内出差过半个月以上。所以我对公司在深圳工作的外国同事并不熟悉。
然而有一天,同事m了一个简历给我:“kiki,这是我一个印度的同学。他现在在深圳工作,能帮看看深圳有没有什么组招人吗?”
“啊,印度人,在深圳工作?”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有些转不过弯来。
“是呀,他以前在tata,公司派他来深圳做项目。后来慢慢地把家人都接过去了,现在全家都在深圳。”
“全家都在深圳啦!现在想换工作?”
“也不是,前几天同学聚会才知道他在深圳工作。而他知道了我们公司在深圳也开了办公室以后,就想让我帮他推荐下。”
“这样呀,好的,我把简历推给我们的招聘专员。”
“你方便加他的微信吗?以后你们直接联系。”那时,印度还没有封禁微信,同事m也下载注册了微信,偶尔我们会聊聊天,生活视频。
“好的,你把我推给他吧。”
没多久,我收到了他的好友申请。我加了他,和他聊了聊。
果然他不是印度教徒,而是基督教徒。所以中国的饮食对他来说问题不大。因为知道我和同事m关系不错,他把他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包括家庭情况。他三年前来到深圳,第二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接了过来。tata虽然也还不错,但是毕竟是外包公司,福利待遇比我们还是稍微逊色了些,而且我们业务线有过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印度人,所以他想试试能不能跳槽来我们公司。
我把简历推给了我熟悉的招聘专员。但见多识广的她也很吃惊,说这是她第一次收到在国内印度人的简历。不过她很快还是把简历给了几个小组,让他们看看有没有可能接收。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印度朋友虽然从事的是Java开,但他一直从事的那个项目系统架构太老旧,和我们这边的技术体系有较大的差别。虽然我们积极地推动面试,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几个月后,大部分有开招聘的小组他都试过了。他自己也感到无望了,就让我不用再推了,他打算在目前的公司继续干下去了。
虽然没有帮到他,但是在几个月的交往中,因为我们和同事m的关联,我们不单单谈工作,还会聊生活,俨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的妻子虽然也是大学毕业,但是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他的工资和我们差不多,请保姆压力不小,能照顾外国小孩的保姆更是稀少,所以妻子只好做了全职太太。两个孩子因为语言和经济的关系,没有上幼儿园。那时他打算过几年上小学就送回印度去上学。
后来因为没有找工作这个话题了,开始还偶尔聊聊天,后来基本上很少聊了。公司大裁员的时候,他听到了消息,在微信上问我:“你也被裁了吗?”
“是的,我们深圳研中心大部分都被裁了。”
“哎,真没想到。”
“好在你没来,否则找工作好麻烦。”
“你找到工作了吗?”
“有几个offer,但还没确定去哪家。”
“哦,那就好。中国太卷了,你年龄和我差不多。”
“嗯,你还好吧?”
“还是老样子,虽然厌倦,但是面试过几家,还不如这里。公司如果裁我的话,我就只能退休回印度了。”
“应该不会的,你们项目只要客户还用,就没事。”
“帮不到你什么,以后有事常联系。”
“你老婆和孩子回印度了吗?”七八年过去了,他孩子应该早就到了上学的年龄。
“没有,在深圳上国际学校了。社区和公司帮忙联系的。”
“那就好,一家人在一起,你也没那么孤单。”
“是的。你也要多保重。”
“谢谢了,以后保持联系。”
虽然这么说,但都是客套话。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他聊过,有时翻到他的名片,也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