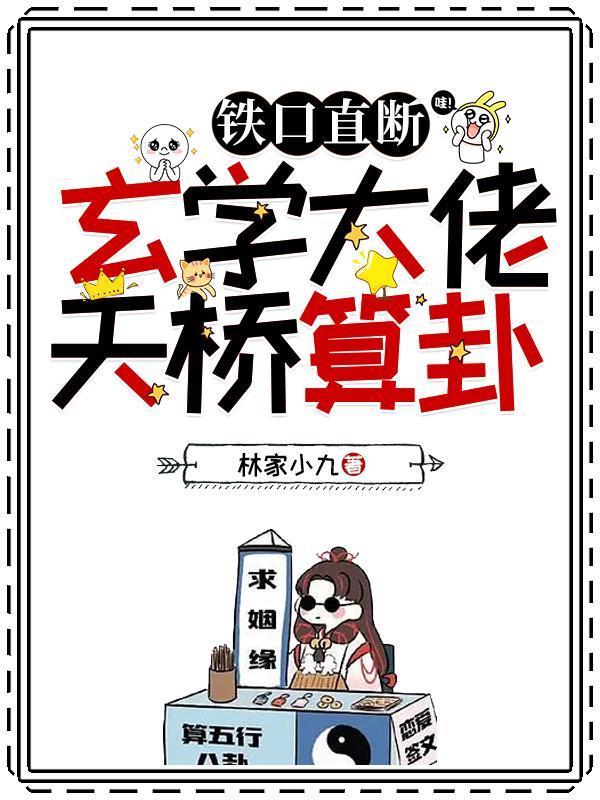UPU小说网>禁欲军官甜宠文 > 第10章 能自己脱衣服吗(第2页)
第10章 能自己脱衣服吗(第2页)
男人先抽出她腋下的体温计,看着飙升到40度的温度,微微皱眉。
沈白榆被扶起来,软绵绵靠在男人坚实的胸膛里。
身上的热气隔着布料烫进男人的皮肤。
“喝药!”
男人抱着她,低垂眼皮,长睫微微扫下,抿着唇线有些严肃。
沈白榆无精打采的抬头,只看到他清晰微冷的下颌线,伸手接过药片,就着他送到唇边的热水喝了药。
陆维远将人轻轻放下,洋瓷茶缸拿走,把医生开的外伤药放在床边。
望着床上的女人,他的思维有一瞬间的中断,因为他还没准备好冲动答应她之后的下一步,比如:脱了她的衣服,涂药。
陆维远拿着药瓶在手心摩挲,看着女人柔弱不堪的身影,半晌没有动作。
部队的单身宿舍和随军家属院不在一处。
陆维远刚才出去找住在宿舍的张副营长借热水。
本想让他媳妇帮沈白榆上药,谁知人家前天便回了老家。
这个点家属院的人早就休息了。
他去喊个嫂子不合适,反而会惊醒众人,引起更多不必要的注意。
虽然这小姑娘说不在乎名声,但他作为男人却不能不顾忌这些。
沈白榆察觉到杵在床边半天没动静的男人,不由睁开眼皮。
见他握着药瓶,漆黑的眼睛望着她出神,她忍不住开口提醒。
“你不帮我涂药吗?我浑身疼抬不起胳膊,早上够不着后背,都没涂!”
她娇娇弱弱的开口,如雨中被摧残的小花,叫人不忍拒绝。
沈白榆身上很疼,尤其是在男人答应她可以跟着他,精神一放松,满身的疼痛便几倍放大,刺激着她的神经。
后背的伤更是跟大火燎过一样,火辣辣的疼。
她在现代哪里受过这种苦。
想到这几天糟的老罪,她鼻头突然涌上酸意,忍了一天的眼泪开了闸,大颗大颗的滚出眼眶。
女人扁着嘴,高烧潮红的脸仰着,满面梨花带雨,可怜巴巴望向他。
陆维远冷静的深眸掠过涟漪,喉结轻滑,终于低低开口,“能自己脱衣服吗?”
沈白榆摇头,她疼,一动就疼。
她难受,不想动,也不想受疼,眼前有个健全的人,何必劳动她动手。
作为病人和伤员,不出力气不是理所应当的嘛!
钨丝灯发出黄色的光芒,在屋内洒出一片平和安宁。
光照在男人脸上,让他略显高冷的脸多了一分柔和。
陆维远咬了下后槽牙,有力修长的手指再一次来到女人的脖颈下。
这一次,他可没昨晚上解她衣服解的利索。
昨夜她昏迷,情况危急,他能趁着她不知情的状态下手。
现在她虽然病着,意识却是清醒,那双含水的眸子还直愣愣的盯着他不怎么文明的动作。
在女人的视线下,手指突然就僵硬的不听使唤。
陆维远压了压眼皮,沉寂的黑眸和她的目光对上。
女人一头乌黑长发如绸缎铺散在枕上,潮红的脸,微张的唇,水雾迷蒙的眼。
再加上他解她衣服的动作,这幅画面怎么看都不清白。
他心跳失控,只不过面上还是一副严肃冷淡的表情。
“闭眼!”
男人下颌微收,发出不容拒绝的命令,仔细听甚至能听出他声音有一丝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