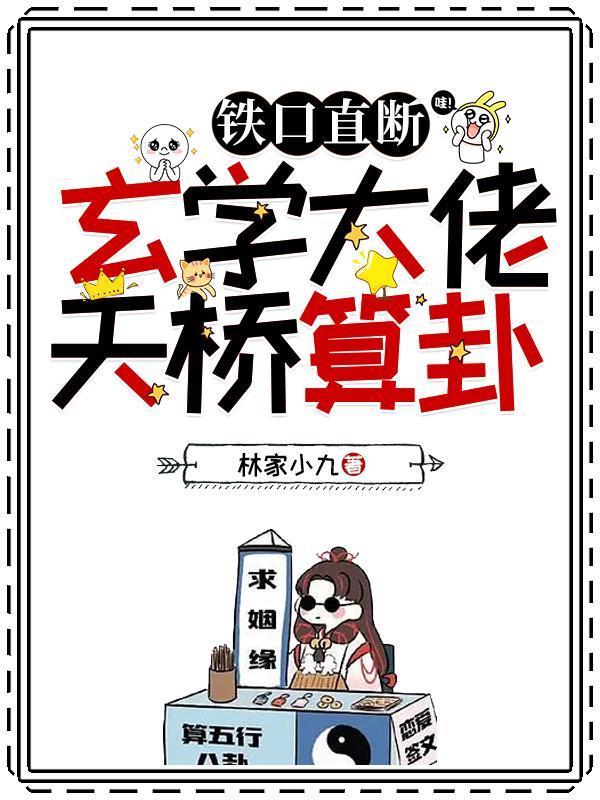UPU小说网>怪物餐厅无限糖果无限金钥匙 > 第75节(第1页)
第75节(第1页)
等到了树林,那就是艾尔莎的地盘了。她用药水催熟植物,制服了追踪而至的狮鹫。然后她在树叶缝隙间看到莱昂重新升空,于是也骑着浮空木,披上一只昏迷的狮鹫作伪装,趁乱冲进对峙的狮鹫群里,假装打斗扑倒莱昂,再齐齐滚进浮岛。
“这是我情急中想到的方法——浑水摸鱼的方法。”艾尔莎拧开药瓶:“别动,让我看看你的伤。”
撕掉粘黏的衣物,肩膀上是三道深可见骨的红肿划痕。药水接触伤口,莱昂轻轻地倒吸了口气。
他带伤面对狮鹫时面不改色,此时却想要向艾尔莎撒娇。
“微不足道的小伤而已,都是因为我大意了。”他轻轻揭过:“他们付出的代价可也不小。”
朝艾尔莎露出安抚的笑容,莱昂半真半假地抱怨,“早知道就不提出兵分两路的提议了,”他得意洋洋地抬起下巴:“才让你错过了我英勇表现的英姿!”
“要知道,我可是单挑了整个狮鹫大军,还赢了个……”莱昂微顿,下意识地避开那场不愿再提起的挑战。莱昂略显慌乱地搪塞过去:“真想让你看看,狮鹫首领那张冷脸碎掉时的模样……”
滔滔不绝的莱昂忽然安静了下来,因为艾尔莎握住了他的手。
莱昂忍不住屏住了呼吸,握住他的手不禁有着少女的柔软,也有历经磨砺后粗糙的茧。
当他被拢在那双温柔又坚韧的手中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在不自觉地颤抖。
但艾尔莎却没有戳穿他。“我躲在云里的时候,莱昂一直没有来,”艾尔莎小声说:“我那时很害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莱昂的目光倏忽暗淡下来。歉疚像压在他心口的大石,他欲言又止,一向伶俐的言语都失去了效用。
他要怎么说的出口,在艾尔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正沉迷在那“勇气的比拼”中呢?
莱昂等待着责怪和抱怨,以此来消解他难以启齿的歉意。
但艾尔莎却总是出乎他的意料,“对不起。”她说。
莱昂看向她,少有地露出迷茫的神色:“为什么要道歉?”
“我太依赖你了。”艾尔莎的表情很认真:“在你陷入危机的时候,我却没法立刻来救你。”
莱昂怔愣在原地,睁圆的眼睛看起来甚至有些单纯的傻气。
“在那种时候,你想的却是……来救我吗?”一贯骄傲的少年抿起唇,眼中的光芒忽明忽灭:“可你不怪我吗?明明是我把你扔在了那。”
艾尔莎的眼眸中是纯粹的信任,“我知道你当时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麻烦。”她丝毫没有怀疑莱昂会扔下她,只是遗憾没能在艰难的时间陪在他身边。“所以下次,不要兵分两路了,我会很担心也很自责。”艾尔莎说,“就算是艰难的战斗,也让我和你并肩作战吧。”
莱昂没有立刻回答,在药水的作用下,他的伤口在迅速愈合。莱昂却反而像是忍受不了疼痛了般,慢慢地低垂下头。
他的额头靠在了艾尔莎的肩膀上,散落的金发遮住了他的眉眼。
“笨蛋艾尔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为什么要道歉呢?”
他差点就要像逃脱狮鹫群那样,狡猾地逃避他的内心。
为什么要这么温柔地道歉呢?让他的卑劣在善意面前无所遁形。可他的心却为此涌起陌生的热潮,他似乎要融化了。
“明明要道歉的,不应该是你才对。”艾尔莎听到莱昂说:“对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他总是追寻游戏获胜的快感,他就不会被轻易地被蒙骗。如果不是他被征服欲蒙蔽了双眼,他就早该看出狮鹫首领隐藏的陷阱。
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他曾问过德尔,对无往不胜的巫师而言,世界是独属于他的游乐场,目标是漂亮地通关。德尔回答他:“总是抱着玩笑的态度,会让你在关键时刻,错失重要的事物。”
心脏还在不规律地狂跳,手也在紧张地痉挛,因为那余留的后怕。
他太骄傲了,习惯游走在危险的边缘追寻刺激,以至于他忘了,这世上依旧存在他无法抗衡的存在——那捉摸不定,却又拥有绝对掌控权的命运。
目睹艾尔莎坠落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所谓命运嘲弄的荒诞。在赢时输,而在失去时才意识到其重要性。
莱昂才像是那个被闪电贯穿的人,在通体的疼痛中迟钝地清醒。
就算他一定要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那代价也绝不能是艾尔莎。
莱昂垂眸,看着艾尔莎披散的红发,纤细的发丝像是会在暴雨中被打坏的蛛网,而他刚刚就是在这钢丝索上走了一圈的小丑,在落入深渊的威胁中,心有余悸地回到彼岸。
“我差点就要失去你了。”莱昂语气低落:“都是因为我……”
“莱昂,你看着我。”艾尔莎摇摇头,捧起他的脸:“我并不是会被动失去的东西,我没有那么脆弱。”
“即便没有戒指,我也不会被那道闪电劈中的,因为我事先就注意到了雷云的存在,我的口袋里还有藤蔓,可以把自己包起来。”艾尔莎露出微笑:“因为你跟我说过的不是吗?要注意天气。我是你骄傲的学生,我也在成长变得强大,绝对不会这么轻易认输的。”
面前的双眸平静温和,如同雨后放晴的月光。但表面下那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是包裹在刀鞘里蓄势待发的匕首。
清澈的月光,凛冽的匕首,统一又矛盾的美。也正是因为此,他才会一直被艾尔莎吸引。
就像德尔说的,艾尔莎和他截然不同,或许她拥有比他更强大的力量。他能看到那珍贵的、宝藏般的光芒,无须挑战来证明其价值。
在这静谧中,莱昂能听见艾尔莎起伏的呼吸和心跳。
规律有力的节奏仿佛能安抚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陌生的热潮再次淹没过他。
许久前,莱昂向噩梦夫人讨要无名蔷薇的花种时,噩梦夫人曾对他说:“无名蔷薇需要的是名为珍惜的情感。我想,这对你来说还太早了。”
“说不定我能做到呢,”莱昂不甚在意地说,“说不定,”他狡黠的目光中划过戏谑的神情,“我能找到珍惜的人呢。”
“哦,看你这轻浮的态度,真是让我头疼。”噩梦夫人露出无语的神情。偷听的德尔也忍不住放声大笑,大声嘲讽:“哈哈!荒诞!下辈子吧!”
所以当阁楼中央,那个自从莱昂抱回来后,就精心照料却毫无动静的花盆。在这个普通的、无人来访的日子,于寂静中,沉睡的土壤忽然悄悄隆动。捕捉到这一微小变化的屋灵德尔简直称得上大惊失色。
德尔不可置信地盯住花盆,花盆却在异动后重归平静。
“这不可能,一定是错觉,”德尔嘟囔:“不过,那臭小子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呢。”
“难道是我老花眼了?”可惜艾尔莎不在,不能帮他擦亮眼睛,德尔又想念起艾尔莎:“艾尔莎此刻,又在哪里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