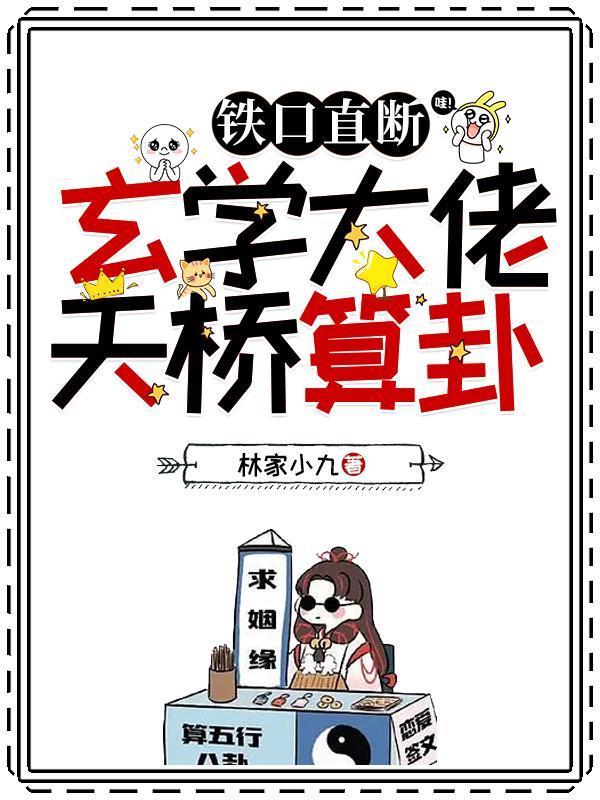UPU小说网>被迫嫁给丑夫后讲了什么 > 第2頁(第1页)
第2頁(第1页)
她聲音剛落,院子裡就傳出開門聲,緊接著是快但沉穩的腳步聲。
轎夫們蹲下身體,準備將轎子放到地上。
轎子隨著他們的動作搖晃的幅度有點大,裡面卻並未傳出任何哪怕一絲輕微的響動,實在是過於安靜了。
為那老轎夫轉頭和其他轎夫交換了個眼神,又看了眼那敲門的婦人。
他們抬了這麼多年轎子,詭異的事也遇見過。轎子裡現在有人沒人心裡更是都一清二楚。
旁人不知道,他們這些轎夫都是看得真真的,那娘從家裡被背出來時,蒙著蓋頭看不到臉,但身上都是軟綿綿的,一點氣力也無,完全是被人強架上轎子的。
這婦人一路上死催活催,估計就是怕半路出事。
還有眼前這戶人家,老轎夫雖不是柳西村人,但也聽聞過這戶主人的事情,這十里八鄉就沒哪個年輕的姑娘或哥兒會心甘情願嫁過去的。
等會轎子門帘一打開,說不好裡面還是不是原來的那個大活人。
到時候這苛刻的婦人說不得要鬧到衙門去,老轎夫不想因為這事受連累,就準備放下轎子立刻跑路。
因為那婦人給的銅板太少,他堅持跟她提前要了全部報酬,如今倒是方便了。
院子裡沉穩的腳步聲停在了門內,眼前的木板門喀拉一聲輕響,有人要從裡面出來了。
與此同時,轎子底部馬上就要落在地面上,就在這一瞬間,老轎夫突地神色一變,腰不由自主躬了下去,其他幾個轎夫更是忍不住趔趄了一下。
嘭的一聲,轎子幾乎是砸了下來,幸虧離地面已經很近了。
等在門口的婦人回頭又是狠狠瞪了他們一眼,為的老轎夫低垂著頭,掩藏著自己臉上的驚駭。
就在轎子落地的一瞬間,本是空空的轎子裡,突然多出一個人的重量,始料不及的他們差點被壓得摔倒在地。
一陣冷風吹過,老轎夫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渾身的汗都變成了涼的,冰冷刺骨。
喀拉,木板門被打開了,老轎夫下意識臉皮顫抖地抬頭看去,只見一個格外高大的男子身影站定在門口。
此時天已經黑透了,看不清這人的臉,只能看到這人身姿挺拔,寬肩窄腰腿長,站在那裡猶如一座俊秀屹立的青山。
這人一照面,那婦人便歡天喜地地迎了上去,絮絮叨叨地解釋:「都是這幾個轎夫不頂事,耽誤了時辰。」又指了指那轎子道:「這孩子太高興了,酒多吃了幾杯,醉得不省人事了,大郎你多多包涵啊!」
那男子向她所指的方向看來,儘管還是看不清臉,但老轎夫依然能感受到那犀利而沉靜的目光。
本來想跑的心思竟一點都不敢提起來了。
老轎夫深深地低下頭去,不敢與對方目光相碰,耳邊似乎聽到了男子聲音低沉,說了些什麼,但一個字也沒聽清。
只用餘光看到那婦人笑著伸手,接過男子遞過來的一個沉甸甸的布袋,她低頭打開一角看了看,頓時臉上的笑容更燦爛了。
老轎夫只看見一點銀光匆匆一閃,那婦人就把布袋收進了袖筒,讓開了地方。
隨即,腳步聲響起,沉穩而冷靜,最後,站定在轎前。
他似乎有過一絲猶豫,但很快,就果斷地伸臂掀開轎子門帘。
那婦人忙小跑著過來,殷勤地提了燈照了進去。
見狀,老轎夫則目露駭然之色,蹭蹭往後退了兩大步,卻又難忍好奇地也跟著看向轎子裡面。
燈籠昏暗的光線中,一個瘦弱的身影癱坐在轎內,他的身形比一般男子纖細得多,甚至在哥兒中也算是瘦弱的。
大紅色的蓋頭將他的頭臉蓋得嚴嚴實實,紅色的嫁衣寬鬆地罩在身上,脖領處露出些白嫩的肌膚來,顯得他更加羸弱。
淡淡的酒味從他身上散發出來,混在轎子裡相對沒那麼冰冷的空氣里散逸出來,竟讓這人看起來有種弱質風流的妖異味道。
雖然如此,轎子裡的人看起來確實還是個正常人,不是什麼可怕的精怪。
只是,當老轎夫疑惑的視線從對方身上,來到腳上時,身體突地微微一震,他記得清清楚楚,娘子上轎時,腳上穿了雙繡鞋,因為衣袍是的,而那雙鞋明顯是舊的,差別明顯,所以他印象極深。
然而,那雙鞋現在沒了。他的目光在轎子內逡巡,根本找不到它的蹤跡。
而掀開門帘的男人在這時,已經彎下了身體,探身進入轎中,將那哥兒從轎子裡毫不費力地抱了出來。
之後,老轎夫只感覺面前一陣風,男人已經抱著娘子轉過身去,像來時一樣,大步往院門內走去。
從他的方向,只能看見娘那一雙只著白襪的腳。
在婦人絮叨的「恭喜」、「早生貴子」之類的道喜話中,男人進了門,木板門也隨之被關上。
在門被關嚴的最後一刻,老轎夫看見一隻潔白纖細柔軟的手,蛇一般伸出,軟軟地無力似的攀附到男人被腰帶束緊的勁瘦的腰上,緊接著,抓緊了那一處衣衫。
老轎夫一驚,什麼都顧不上了,忙叫上其他幾個轎夫,幾人抬起轎子,飛一般逃離了這裡,不管那婦人如何叫他們,只當聽不到,直往村外而去。
本來想讓他們捎帶著自己回家,見狀,那婦人氣得直跺腳,恨自己報酬給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