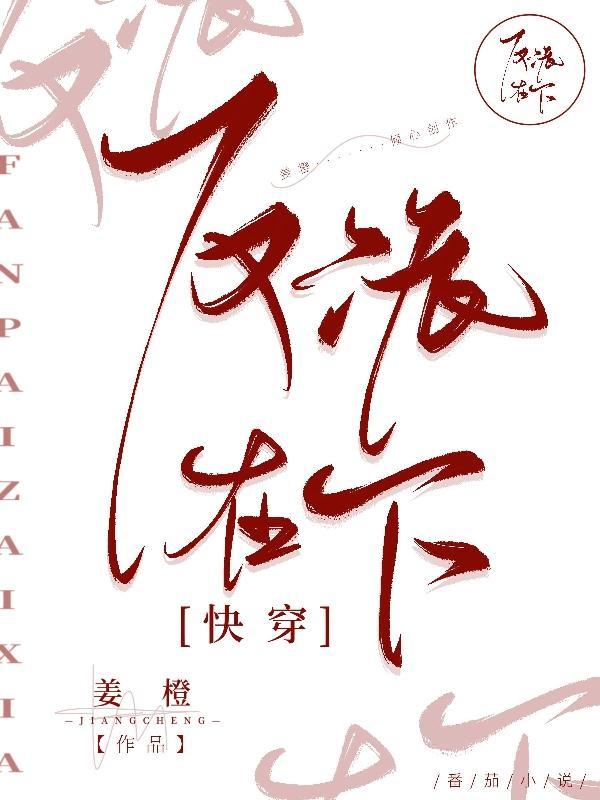UPU小说网>魔渡之剑痕皇权全文免费 > 第二十五章 密会(第1页)
第二十五章 密会(第1页)
青衣的中年男人从赌坊出来,提着包袱来到了外面。
正巧看到于仲亭一行人押着嫣然雪从街头走过。
他神色瞬显吃惊,连忙退避到了巷子角落。
所以那一行人并没有发现中年男子。
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人们纷纷为较武堂的兵卒让行,在帝都可没有人敢得罪较武堂的人。
嫣然雪被两个兵卒分别从两边押着,她目不斜视,神色只有淡定从容。因为心中有一人,她信任凤拂樱会救她。
看着一行人去往的方向,中年男人心道:“这个方向……莫非是政枢府……”
最后那些人押着嫣然雪来到了政枢府。
政枢府建造的十分恢宏大气,红墙绿瓦,假山亭台,柱子雕龙绘凤,宫灯盏盏,十分富丽堂皇,毕竟是帝都理政处,所以建筑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
中年男人跟踪于仲亭等人来到了政枢府,这也证实了他的猜测。
最后他若有所思,心下有了计量,默默离开了。
夜晚,在东陆与西疆的边境交界处,那里有一道绵延不绝的长墙——止戈之墙,那是东陆收复西疆后铸建的城墙,止戈,寓意再无战乱之意。
此地从此也就以墙为名,也因为地段偏僻,所以很少有百姓在此居住,也一直很平静。
然而近期却有些不寻常,偶有狂风吹过细沙露出白骨,再不然就是经常出现血红色雾霾,还有一些幻境浮现,出现的次数很少,但是一出现,近点的地方就会牛羊死亡,就连人员也会伤亡。幻境多为朦胧不清且变幻不断的,有人路过此地说远远的见过一次幻境,那是如同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一瞬即逝。
而今夜止戈之墙,似乎不太平静。原因无他,不过是下起来一场雪雨。
雪中有雨,雨中有雪,还有寒冷的风。冰凉刺骨飘然落下,积在止戈之墙下的路面,可能是雨雪缘故,又刚下不久,也没有累积,边境道路泥泞非常。
一人一手打着灯笼,行在边境止戈墙下。微黄的灯笼光色也只够照亮方寸,光亮映照在行人黑色的靴子上,他踏过水坑,皮靴上不免沾染了泥水污渍。
那是一个暗夜行者,顺着黑色靴子往上,只见那人着一身黑色简服,头顶戴着一顶遮雨斗笠,又加上是夜晚根本看不清面容,只能从身形穿着判断出是一个男人。
他驻足,立于墙下,任由冰凉的雨雪飘落,衣服也有些湿了,他望着长墙一方,似在等人。
不多时同样头戴白纱斗笠的一人走来,由远而近。
“你来了。”等待的男人看到来人率先说道。
“嗯,事情办的怎样?”回答的是一身青色素衫的女性,声音几分苍老,听起来是个将近五十来岁的老妇。
“差不多了。”男人说着,从腰间取下一件黑色裹布包裹好,长三尺有余的东西交给了对方。
“不会引人生疑吗?”老妇问。
“不会。”男人回答的自信,语气亦无波亦无澜,很是平静,“告诉冥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了。”
老妇收下那黑布裹着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回西疆?”
“现在还不可以,我还有事要处理。”
“现在很危险。”老妇担忧。
“不用担心我,如今局势越乱对我们越有利。愚昧的人只道得极莲者方可纵横天下,却不知极莲神剑还有一个秘密,所以我敢断定穗光皇帝一定会想方设法得到神剑。”中年男人道。
“就算如此,他们迟早也会发现。”老妇道。
“一切尽在掌握,自会有人替我们背锅。”男人胸有成竹的说道。
“可是城主已有两年不曾回西疆了。政事全部交给冥陌打理,有这个城主我看也跟没有一样,哎!”老妇叹息一声,又道:“只可惜善战的冽羽军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薛氏又算什么?而烈羽家的后世子孙亦失踪多年不知生死。”
“城主那里我会想办法找到他,而烈羽家后人已失踪这么多年,茫茫人海,我估计凶多吉少了……”男人叹息道。
“是啊!不提也罢,倒是你,办完一切便归乡吧。这么多年漂泊异乡也是难为你了。若暴露身份,对你恐无利,西疆不能没有你。”那老妇语气带愧歉,还有一份担忧。
“生死,比起必行之路,又算什么。在我决定踏上这条路时,便把一切都放开了。我的立场便是忠于西疆。”男人说道。
“是阿,人的立场一旦注定不可更改。但是我感觉的出来,你任有一份愧疚之情。”老妇说完,随之从头上取下木簪,喃喃念了个诀,那件黑裹布包着的东西竟然泛起一瞬耀眼的白光神奇地被吸入了那木簪里!之后老妇便将木簪又别在了头上。
这是西疆人的一种术法,用特制的藏物簪,来收纳贵重的东西。
“愧疚也比任由东陆予取予求的好。若非三百多年前,东陆人偶然得隐世高人指点建造天枢仪器,我们又怎么会输。我们西疆本就不该臣服他人之下。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历代白骨都要讨算个黑白功过,如何追究?不过立场问题。”黑衣男人微微转身,冷冷说道,帽沿的有雪雨化水滴答落下。
冰冷的雪雨,寒冷的冬夜。跟暖阳白日形成鲜明对比,就如同黑白正邪,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立场的恒河,跨越不了。也终究改变不了,黑夜白天不能并存,也如同一片天空下月亮与太阳始终不能同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