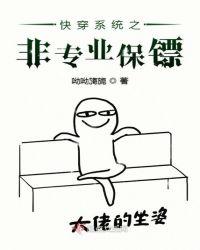UPU小说网>三少爷的剑之慕容秋荻素衣音尘 > 第44页(第1页)
第44页(第1页)
慕容秋荻隐隐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咬牙道:“我不想做的事也没人能逼我去做!”语罢,她便走出门去,对着楼下的小二喊道:“给我拿两个热的熟鸡蛋来!”
与其和他在这里打口水杖,不如先拿鸡蛋赶紧给眼睛消肿。
谢晓峰坐在窗边,临窗眺望,能看见不远处的河流,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
他想着慕容秋荻刚刚的话,有些发怔。
“我不知道你为何要折磨自己,若是心里有愧疚有伤痛,这样折磨莫非真的有效?”
那些不能向人诉说的隐痛和永远不能平愈的创伤,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都已几乎忘记——至少他全心全意都希望自己能忘记,还有谁知道?
他其实没有忘记。
他只是心灰意冷。一种深入骨髓的疲倦不知什么时候,一点点地沁入,让他逃无可逃。
所以他才要变成阿吉,他甘愿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只为能够找到一条出路。
可惜他没能找到。他又变回了谢晓峰。
但他又不是那么愿意。所以,他是谢晓峰,可是又不像谢晓峰,谢晓峰该是聪明健壮﹑英俊潇洒的,但现在的他依旧很穷,穿着一身质地粗糙的衣服,还是在到处游荡,不过他自己知道,他的游荡有一个中心。
谢晓峰将目光投向那个正倚在床榻上拿鸡蛋在眼上滚来滚去的女子。
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片绿草如茵的山坡,她就在那棵大树下,朝他一剑刺来,他抓住她的手,她对他嫣然一笑,道:“你是谢晓峰?”
“除了谢晓峰,没人能接得住我这一剑。”
她美丽的容颜在扑向他怀中的时候瞬间绽放,他记得,她轻软的身段,纤细的腰肢,倾城的笑靥。
他尚记得她第一次躺在他身下的时候,那娇羞又紧张的姿态,他尚记得她第一次攀上高峰的时候,那妖娆而迷醉的神情。
他有过很多女人,他记得她们,但唯独她,哪怕只是一颦一笑,一个动作,一个喜欢,他都记得。他记她记得最清楚。
可惜她却早已不在乎。
十年,他已经和这个女子纠缠了十年。
谢晓峰一直认为,他是天生就应该享受女人宠爱的男人,在他眼中,女人只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工具,当他需要她们时,她们都会像猫一样乖乖投入他怀里。当他厌倦时,他就会像抛垃圾般将她们抛开。他从不相信任何女人。对这一点,他从不隐瞒,也无从歉疚,因为他根本不在乎。
慕容秋荻,她是唯一的例外。
她是不同的。在他心里,她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取代。
因为这份不同,她比其他的女人更苦,他爱她爱得越深,抛弃她的时候就愈加无情。
难怪她巴不得离他远远的。
谢晓峰微微苦笑,纵使已经过了十年光阴,他依旧忘不了她。谢晓峰很清楚,对他而言,无论她是好是坏,无论是谁负了谁,他只有和这个人在一起时,才能忘记那些苦难和悲伤,心里才能安宁。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感情。只知道人与人之间若是有了这种感情,就算是受苦受骗,也是心甘情愿的。
就算死都没关系。
但即便他死,她也是不屑一顾吧。想到这里,谢晓峰觉得舌头有些发苦。
如今,一厢情愿的只是他,她活得很好,如果没有他,她会活得更好。谢晓峰望着慕容秋荻美丽的身影,心下感到疲倦﹑怅然和失落。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他既然已经决意抛下她,为什么现在又放不下?
因为小弟吗?
不是。谢晓峰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的秋荻,不会算计他,也懒得算计他,她对他唯一的希望,大概就是他永远消失在她面前。但近来,她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被这种情况给折磨着,只有看到她,他才觉得安定和平静。
如果慕容秋荻知道此刻谢晓峰的心中所想,她一定会觉得这个男人很犯贱。
作者有话要说:万圣节快乐啊筒子们!晚上去爬山了,刚刚回来,感觉很不错
存稿木有了,咱们换榜见阅读该文章的读者通常还喜欢以下文章
秋荻有点不太对劲。
慕容秋荻靠在马车内的软枕上,手中拿着用来消遣的书,眼珠子却时不时地在瞟向窗外。
谢晓峰这一路都看在眼里,早上他就发现她就不太对劲,做什么都有点心不在焉,终于他忍不住问:“你有事?”
慕容秋荻愣了愣,随即轻轻摇摇头,干脆闭上眼睛躺下。
谢晓峰绝不是会自讨没趣的人,见她不回答,他便也不会再问。
一路无话。
马车行至一处村庄的道边,路边便是大片大片的水田,初夏时节的稻苗绿油油的,长势正旺,田间的小路上有孩童在奔跑嬉戏,发出阵阵笑声。
慕容秋荻掀开窗上的帘子,往外望去。
“停车。”
“我下去走走,”慕容秋荻推开车厢的门,转头看了谢晓峰一眼,淡淡道,“你要来么?”
行走在狭窄不平的黄土路上,慕容秋荻步履从容,似乎还很熟门熟路。
清新的风拂过面颊,深吸一口气,只觉空气里仿佛都带着甜香。
“这不是……秋荻妹子?”不远处,一个扎着头巾的健壮妇人,挎着一个大竹篮,站在田埂上,惊奇地往这边看来。
慕容秋荻颌首微笑,道:“李家婶子。”
那妇人的脸上立即露出喜色,她快步朝这边走来,一把握住慕容秋荻的手,亲亲热热道:“啊呀,真是秋荻妹子!我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秋荻妹子这身打扮,真像天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