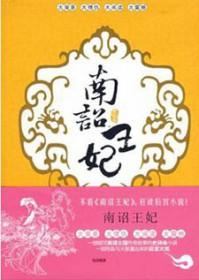UPU小说网>灵魂狱卒怎么打 > 第46章(第2页)
第46章(第2页)
“不离,不签,别耍手段,你走不掉。”谢秉川一口气说完,打开门背上包离开了。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连给他说个“等等”的时间都不剩,回过神来视线里早就没有谢秉川的身影了。
余温言不信邪,拿出手机给谢秉川发消息。
有了昨天前车之鉴,这回就算鸡同鸭讲,他也要一口气全发出去先。
余温言编辑了足足十几行,按下发送键时,却只看见鲜红的感叹号。
还有一行字:消息未送达,您已被对方拉黑。
余温言:“……”
这下连对牛弹琴的机会都不给他了。
骤然觉得好笑,余温言蹲在床边,摩挲着腺体,笑意沉至眼底,很快消散不见。
既然真相如此,每逢他问起时,谢秉川又为何总是遮遮掩掩,闭嘴不言。
一句“你没法终身标记”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可谢秉川却从不说。
余温言思考着从谢秉川嘴里骗出真相的方法,后腰又一阵疼,余温言弯下腰去,缓缓扶着柜子边蹲下,脑海中顿时充斥满各式各样的声音,同昨天一样。
又来了。
余温言眯了眯眼睛,意图隔绝声音,可声音直达脑海,遮耳朵不成效。
乞求雪松柏症消失的,乞求家人平安无难的,乞求温度别再下降的,乞求为满足自己私欲。
应有尽有。
这回不怎么杂乱,却仍旧伴随着难以抵御的耳鸣,标记发烫发疼。
余温言咬着牙,等着这阵子过去,听着村民们的乞求,他只觉得头疼欲裂,似将庙宇的监控器装在他的身体里,还是个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监控。
不知道过了多久,昏昏沉沉间,余温言听见熟悉的声音。
谢秉川上供上香,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虔诚合眼,将指尖抵至鼻尖,微微低头。
他是去还愿的。
“感谢山神,我见到他了,愿心已了。”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祈愿。
余温言微微将眼睛睁开一条缝,胎记疼痛感被分走,温度不再滚烫,他指尖无意识刮过地板,抓住散落一旁的衣服。
他此刻只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对讲机,对着远在不知道几公里外、雪山脚底庙宇里的谢秉川大声喊,喊他就是余温言。
耳边声音渐息,余温言莫名其妙觉得累,有些困倦,可他明明才刚睡醒,能睡是福,余温言没作挣扎,放任自己再度坠入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