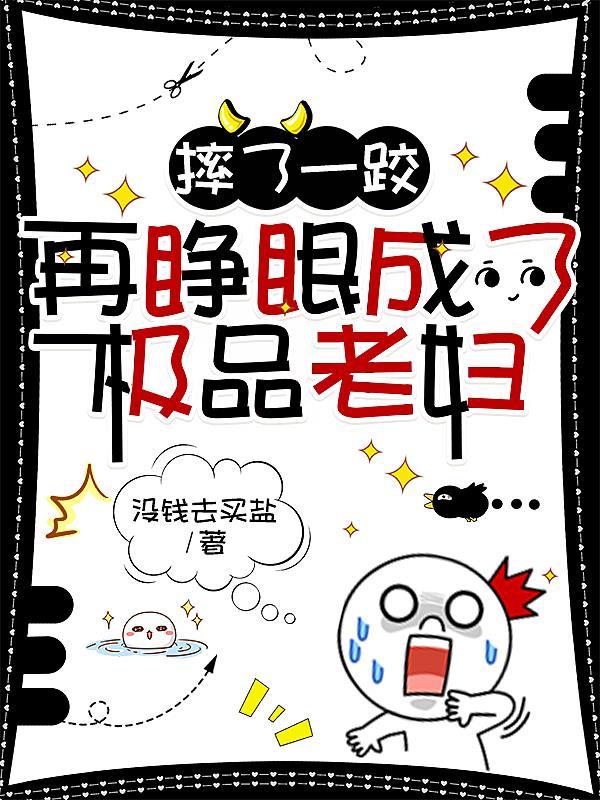UPU小说网>我真的不想演by白孤生 > 第34章(第3页)
第34章(第3页)
“比本应该的多。”
多么稀罕,此时此刻少司君又变作有问必答的好人了。
他惯会有这样的手段。
灵活地在两个极端里跳跃,疯狂而至于正常,不过一体双生。
只是这样的手段不常用,毕竟少有人值得他这么做。就如同他利用自己的脸,少司君也会自然地将其用在阿蛮身上。
而阿蛮呢,在听了少司君的话陷入沉默。
他想起宁兰郡的司君,那人是那么正常,每次朝着阿蛮笑起来的时候总是那么明媚鲜活,顶多就比较爱粘着他;他又想起少司君屠了谙分寺回来的那一夜,男人在屋顶上险些失控又压抑下来的克制;他还想起庆丰山上的雨水,与夹杂在雨幕里近乎兽类的咆哮……
这于少司君而言,的确是诅咒。
“……你从来都没有吃过,”阿蛮的声音有些轻飘飘,像是那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是吗?”
“是呀。”少司君稳稳地承住了阿蛮的那句话,“从未有过。”
平静到极致的嗓音底下,却是潜藏着难以克制的阴鸷与暴戾,黑暗的焰火无时无刻都不期盼着挣脱束缚,成为燃尽一切的大火。
可少司君又怎么会让它们如愿?
少司君并非排斥怪物。
他自己,便是那头最疯狂强大的怪物。
可这身体是他的,那这欲|望也得臣服在他脚下,哪怕暴虐狂躁的怪物,也必需朝着他摇尾乞怜,哪有它们放肆的权力?
于是他掐住欲|望的喉咙,践踏饥|渴的躯体,粗暴地将它们逼迫到无能为力的地步……
是的,阿蛮恍惚地意识到,少司君的确会问出那句话。
他为什么没杀了阿蛮?
为什么呢?
阿蛮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也曾扼杀过无数人的手,身为一个死士从来无辜不到哪里去,说到底他也是恶人一个。
而现在,就连阿蛮自己也好奇,他到底是哪里让少司君感兴趣?
“想不通吗?”打破寂静的人,是少司君自己,“没关系,我也想不通。”
他站起身来,在这黄昏交接之时笼罩下来的影子,叫这方寸之地无形间变得逼仄,变得更像是一个囚牢。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阿蛮很想为少司君给出来的宽裕时间感到高兴,可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停留在男人敢为人先的膝盖上——意思是,为什么少司君要上床?
少司君混不在意阿蛮那一瞬间戒备的模样,他向来自我。
他不仅上了床,还伸手按住阿蛮的肩膀。
“……大王能下去吗?”
“不能。”少司君奇怪地反问,“那岂不是白上来了?”
“……所以您上来到底是干嘛呀!”
阿蛮试图冷静,可他总觉得少司君是故意在他的忍耐边界蹦跶。
少司君镇定自若地说:“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