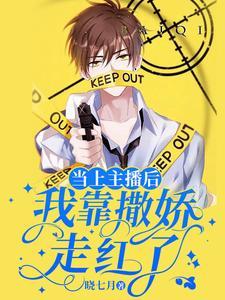UPU小说网>夏歇计尔笔趣阁 > 第149节(第2页)
第149节(第2页)
夏仰身上还穿着那件舞服,穿得规矩,纯白色的内衬尺寸紧贴青涩的身材曲线。被他一扯,腰带直接掉在地板上。
她锁骨被粗砺指腹摩挲着,一惊,皱眉推他:“我没洗澡。”
段宵一只手握住她两个手腕,舌尖也趁机撬开她嘴。舔弄了一会儿,又吻得重,像是在占有,又像是缠绵的想念。
他含糊地说:“够香了。”
他就是故意在磨夏仰,因为她前天晚上挂了他居心叵测的电话。
可谁让他每次一和她异地、异国,脑子里就总想些歪门邪道的路子来抒发情欲,花样都不带重样的。
但夏仰又不敢再推他,怕他手劲一大撕坏她衣服。
上一回就是才录完节目,他开车来接她。嫌她身上的舞服细带难解,一点耐心都没有。
她都提醒说全世界就这两件舞服。
弄坏得让他去买来另一件代替,很贵。
段宵一点也不当回事儿,扯坏后,还来了句:“行,现在全世界就一件了。”
“…”
门口玄关处装的是感应灯。
黑了后,又被一下一下地撞亮。
夏仰本来练一天功就够累,回家还被他深深浅浅地弄了一顿,从累变成困加饿。
被抱出浴室的时候,她胸脯起伏还剧烈着,不忘拉着他提要求:“你帮我写作业。”
“好。”
“要全文翻译的。”
“可以。”段宵答应完,又说她没出息,低声笑,“多少年了还要我教作业?”
她埋在他颈脖那,像小动物似的蹭了蹭,小声抱怨:“多少年我也没变学霸啊。”
他被她下意识的动作弄得也柔软,笑得胸膛在颤。亲她耳尖,缠吻了好一会儿,摸着她小腹问:“晚饭想吃什么?”
夏仰两条手臂懒洋洋地挂着他肩膀上:“你做?随便弄点吧。”
段宵留学那一年多里早就会煮菜了,厨艺进化得也不错。
夏仰依然没进过厨房,这辈子也没做过几次饭。对她来说最大的家务是处理五点半的洗浴和换水工作,但这也不算麻烦。
他们结婚后,一家两口和一只猫的状态迟迟没变过。
倒是温云渺在实习之后,被外派了分公司。地点在隔壁省,让夏仰好一顿操心。
直到温云渺谈了个挺靠谱的博士生男朋友,她才不好意思隔段时间就问人状况。
陆嘉泽那群朋友还是一样,继续念书的念书,接管家业的也没闲着。一群年轻人还是经常一起开车出来聚一聚,带着各自的新伴侣。
但绕来绕去的这几年里,最稳定的只有段宵夏仰这一对。
他俩的故事在圈子里已经被传得乱七八糟。
要怪只能怪陆嘉泽和许霓吵架时胡乱丢出去些信息,被有心人断章取义,什么版本都有。
夏仰读研二快放寒假的那段时间里。
倒发生件不大不小的事。
全国各地罕见怪异天气,京州也不例外,入冬以来居然连续下了多日暴雨。城市内部雨水泛滥成灾,给底层劳动业造成不少损害。
段氏在这种天灾面前都要发挥龙头企业精神,捐钱捐物资。
那天夏仰本来是开车去公司给段宵送份文件,但路上遇到搭载孕妇的车坏了,司机正在找人求助。
她没多想,立即让孕妇上了车。
一路为了赶速度,甚至闯了两个红灯,可还是来不及。
人站在手术室外,听见主治医生说孕妇难产大出血。
家属没来,正规医院根本不会问保大保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直接保母弃子。
等孕妇的一家人及时赶到,也听到孩子没了。
那位丈夫居然把矛头转向夏仰,质问道:“你开的什么车?”
“是不是撞到哪儿了?我媳妇儿平时身强体壮的,怎么可能保不住我儿子!”
“这事儿你跑不了,绝对要付责任!”
段宵和孕妇那边的家里人几乎同时到的医院,那会儿来做笔录的警察也到了。
他们一来,对面那男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孕妇的家里人指着男人鼻子骂骂咧咧,无非是说他苛待妻子才酿成今日大祸。
病房门口哭的哭,嚷的嚷。
刚做完手术的孕妇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