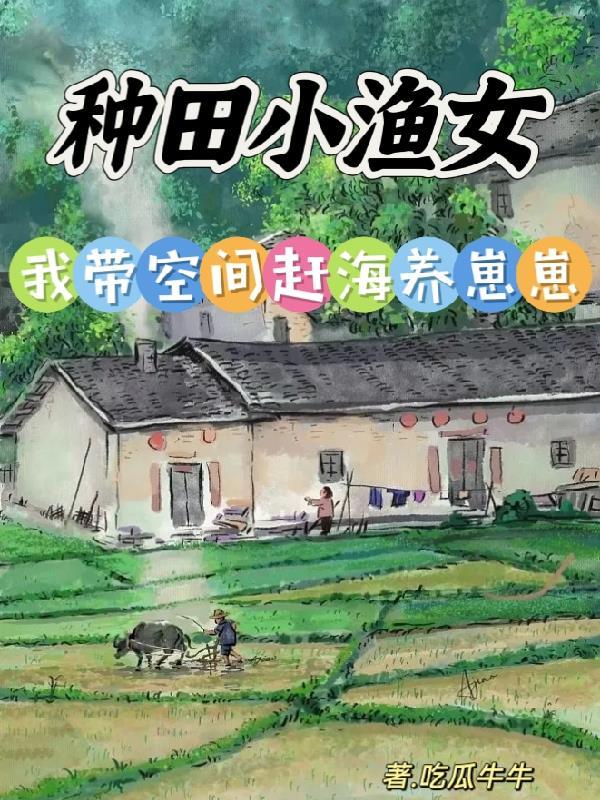UPU小说网>被权贵送人后我封心魏婉 > 第23頁(第1页)
第23頁(第1页)
卞如玉上下眺了兩眼,掏出一隻絹帕,擦拭洞簫,尤其吹口,反覆擦了又擦,檢查數遍,才將唇湊近吹口。
她剛才吹得什麼玩意?雖有情卻無技藝,錯了三個音,氣也短,一聽就知道是沒吹過幾的手,還敢在他面前獻拙?
卞如玉覺得自己一定是容不得出錯,才會給魏婉糾正示範,絕不是因為別的什麼。
一氣吐下,氣震指顫,如風穿洞,愴恍惻惐。
魏婉靜聽,亦默默凝視卞如玉。
小巫見大巫,他遠比她吹得悅耳高明,不僅肺氣充沛,不似病人,且簫技爐火純青。魏婉兀地靈光一閃:他真正喜歡的樂器不是阮琴,而是洞簫!
他應該……也不是真地喜好徽調。
魏婉突然間推翻了許多事,不禁泛起寒意,雙臂甚至起了雞皮疙瘩。吹奏完的卞如玉偏在這時放下洞簫,尋到魏婉目光,對住。
對視片刻,如兩條交匯的河流慢慢融合,卞如玉嘴角笑意逐漸斂起:「學會了嗎?」
魏婉身不動,只唇張合:「奴婢再不會吹錯了。」
少傾,又道:「殿下吹得真好,仿若有一片簫心。」
卞如玉突然不自覺地漾起嘴角,緊繃的眉眼舒展開,似乎終於等到自己想聽的話。他猜到魏婉又知曉了一個秘密,卻不惱不懼,反而有種自己也揣摩不透的開心。
魏婉亦不道破。見卞如玉喜笑顏開,她也高興自己用對了心機。
窗外響起落雨聲。
卞如玉扭頭循聲仰望,淺淺笑嘆:「呵,竟然是雨。」
魏婉懂他的意思,是雨也是羽,五音最後一位,恰是雨水的水音,亦為羽調。
魏婉再注視卞如玉,也左偏仰頭,朝同一個方向眺去。春雨飄搖若線,檐淌如簾,料料峭峭,淅淅瀝瀝,下一場潮濕的夢。天色陰沉,染就一片霧靄。
屋內靜悄悄,阿土早退到門前,遠遠隱匿,臥房內只留下魏婉和卞如玉靜坐聽雨。
寂寥孤獨卻又瀟瀟灑灑,洗淨了凡塵,覓得片刻心安。
卞如玉彎腰探手,自腳踝起一順往上揉,再順沿經絡,從上往下回敲。推拿完左腿又捏右腿,目光無意右掃,突然發現魏婉正盯著瞧。
她都看見了!
卞如玉面色頓訕,心猛地一沉。
他雙腿殘廢,久坐輪椅,如不時常推拿便會萎縮,但又不願假以人手,這麼些年都是自己揉捏,自覺屈辱苦痛,十分戒備,連阿土阿火都迴避,更不允外人知曉。
方才卻在魏婉面前忘形!
他心裡突然生出一股從未有過的惶恐,惴惴不安,繼而又惱怒地想:殺了她。
他的手仍放在腿上,低著腦袋,雙眸在魏婉看不見的地方翻滾殺意。
「殿下?」魏婉婉轉輕喚,假意的關切中,有幾分唏噓眾生皆苦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