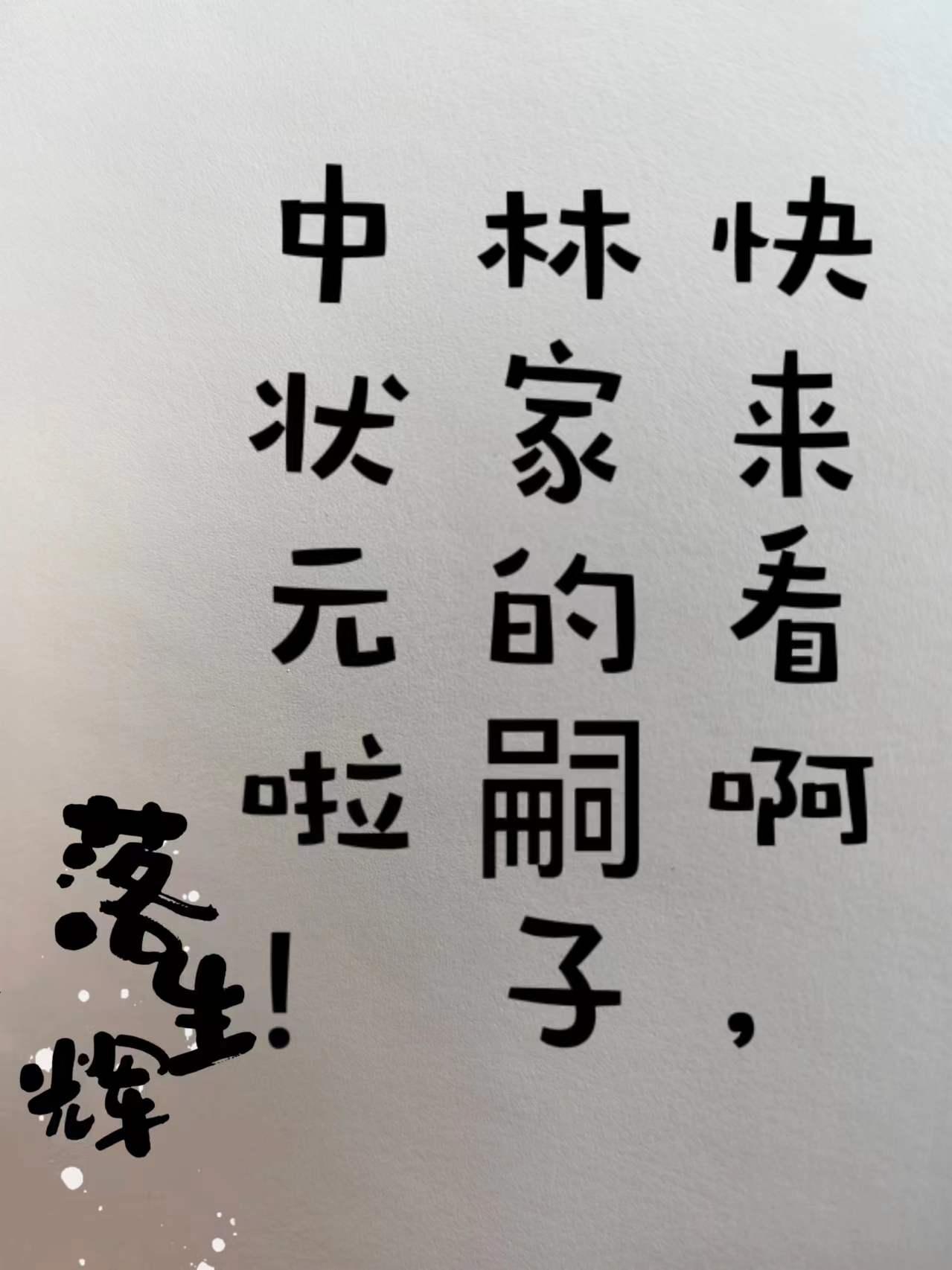UPU小说网>寄我某颗星笔趣阁 > 第27章(第2页)
第27章(第2页)
沈轲静静地看着她,问:“你是在安慰我吗——因为你看到我家有多穷了?”
她挠了挠脸,“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如今阮季星回想起来,才意识到,她也许伤害到一个青春期男生的自尊心了。
太像是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施舍同情心了。
那天,逛完天文馆后,下起了雨。
季曼打电话来,问她在哪儿,叫司机接她回家。
他们没带伞,在便利店门口等车。
阮家的车并不奢华,普通的黑色奔驰。
阮季星说:“去我家吃饭吧。”
“不了,我还要复习。”
“那我们送你回家。”
沈轲还是拒绝:“我坐公交车就行。”
阮季星知道这人犟起来跟牛似的,也没勉强他。
她叫司机把伞留给他,自己钻进后座。
车门刚关上,他又叫住她:“阮季星,等一下。”
沈轲折回便利店,买了一盒薄荷糖,从窗户递给她。
他的伞拿在手里,没打,她看见他肩头、额发被雨淋湿了些,像一只……被丢弃在路边,无家可归的小狗。
又不是不等他,跑那么急干什么。
他说:“晕车吃这个,可以缓解一点。”
“好。”
阮季星催他:“你快回家吧,要是感冒了,考试没考好可别怪我。”
沈轲撑起伞,往后退几步。
她从后视镜中看见他的影子越来越小,拆开包装,倒了两粒进嘴里。
结果,之后她就忘了这句话,忘了晕车要提前准备。
所以,他是记得她晕车,才给她薄荷糖的么?
阮季星一时分不清,他到底是讨厌她,还是不讨厌。
谢晓羽小声问:“星星,你和沈轲小时候就认识了啊?”
“嗯,不过上高中之后,我们就没见过面了,所以跟陌生人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感觉他对你挺特别的啊。”
阮季星说:“可能是因为,我妈妈以前对他妈妈特别好,他念旧情吧。”
谢晓羽半信半疑:“这样吗。”
“不然你以为是为什么?”
想到沈轲自己说没有喜欢的人,谢晓羽又打消了疑虑,摇了摇头。
避嫌
联谊那天之后,阮季星注意到,冯清莹和沈轲的接触多了起来。
但她的路数和庄卉冬不同,她不送礼物,也不黏着他说话,而是不厌其烦地在碰到面时,和他打招呼。
冯清莹很优秀,老师在课堂上有时会抛出问题,可以加平时分,她答得积极,因而深受老师喜欢。
后来,不知从哪里流出消息,说她爸爸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的主任,同时也是经管学院里一位颇具声望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