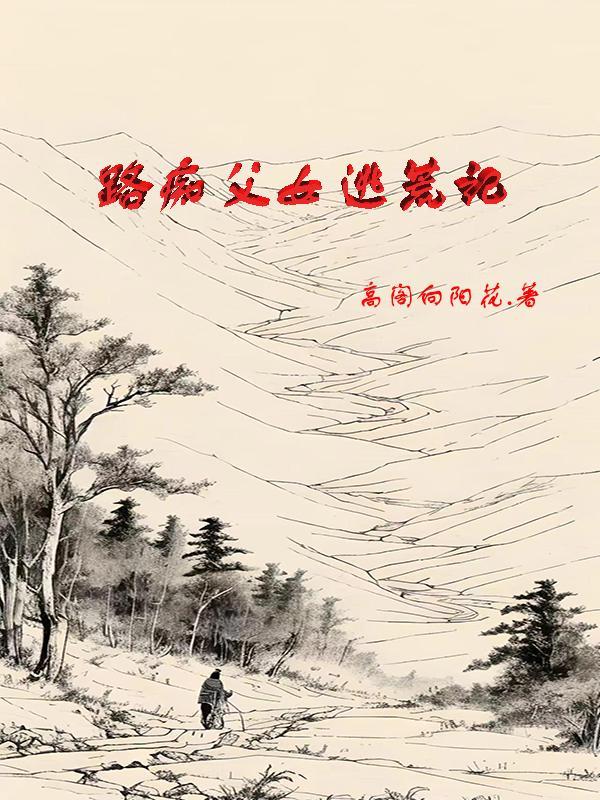UPU小说网>沾洲叹废文 > 第103章(第2页)
第103章(第2页)
祝神摩拳擦掌,贴着墙根去到角落,把墙洞前头用以遮掩的几个大石块搬开,再匍匐到地上€€€€昨日落了一场春雨,今早天才放晴,墙角地上聚着不深不浅的水洼,方才便早已浸透了祝神的鞋袜,只是他思绪激荡无从察觉。此时祝神的膝盖跪在地里,带着春寒的雨水透过衣衫仿佛快冻到他的骨头,两条落了病根的小腿这才后知后觉地起阵阵剧痛。
祝神咬了咬牙,一个劲儿想着忍忍,等出了这地方管它痛死疼死也不影响什么,到时候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锯了都没人管。
他双肘支地,膝盖以下由于犯疼实在使不上力气,便把力道全用在手上,以一种狼狈的姿势钻过了墙洞。
洞外祝神也观察过,围着墙是一圈花圃,偏巧他钻出来这地儿是个拐角,左右种了两树桃花,正好把他挡住€€€€祝神简直奇怪,这么大个府邸,随处可见的是最普通的桃树,栽种得也无规律,像谁随走随插的一般。
他一身脏兮兮地钻出来,隔着花圃只见到前方大片空地上人流涌动,目之所及只到人小腿,望到的皆是品级看似十分上等的衣料鞋履。
祝神心想:果然没能出府。
不过眼下前方人多,也够他趁乱开溜了。
岂知他视角受限,完全没注意到右侧花圃尽头有人踩着泥土地朝他走过来。
片刻后,祝神活动活动被冻僵的脚脖子正打算起身,忽听头顶一个清脆女声道:“……祝老板?”
他蓦地一愣,缓缓抬头,与一脸震惊的疏桐四目相对。
疏桐这一嗓子不高不低,正好够周围一圈人驻足停望;最外头这一圈扭头看过来了,连带着后方所有人都66续续朝祝神望去。
€€€€几日前,贺兰明棋广名帖,邀请北方众多名门望族前来飞绝城参加寿宴。这宴席明面上是为她庆生,实则是贺兰明棋给自己接任贺兰氏家主一事造势,了请帖就是是探口风,来的自然是愿意支持她的;不来的,日后记上,也方便她铲除异己,为将来统一北部铺路。
祝神的墙洞,正好挖到了贺兰明棋请客的这一座园子。
此时整个沾洲大半个北部的名士,男男女女聚在一处,目光齐刷刷拢在了这一个角落里。
祝神不认识疏桐,不认识任何人,甚至听不懂她嘴里那一声“祝老板”怎么回事,但他隐约在心中预感到,大事不妙。
并且当务之急是先从洞里爬起来。
于是他当着一众贵客的面,强忍着腿骨伤寒,扶着墙慢慢站好。疏桐见状,连忙搭了把手,同时给身侧的侍卫麻利地使了个眼色。后者当即一调头,往隔壁院子里冲去。
现下祝神扶着疏桐,站在墙角两株桃树交枝的下方,一身碧蓝色的衣衫的下摆像从泥水里才捞起来,连带脸颊和鼻尖上也多了几抹干巴的泥点子,活脱脱一只在泥地里滚了一圈被当场抓获的白猫,浑身上下除了眼珠子就再也找不到干净的地方。
不多时,眼前的人群从末端渐渐让出一条小路,贺兰破手里还拿着一卷图纸,急匆匆穿过人道赶来花圃前,瞧见祝神这副模样先是怔了怔,随即又上上下下把人打量了几遭,粗略将祝神身上还看得清的部位检查了一番,确认没有外露的伤口才粗浅松气。
祝神低着眼睛,试试探探抬起目光瞄了贺兰破一眼,跟对方视线撞上,当即又低下去,只下意识地松开了抓着疏桐的那只手。
过了片刻,他又瞄了贺兰破一眼,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完了。
人群里慢慢响起窃窃私语。
“这就是……十六声河的祝老板?”
“……像是呢。”
“……怎么从这儿进来?难不成没带名帖?”
“……不过长得可真是标志啊€€€€当真是他?”
“若真是喜荣华那位,可见传闻也并非尽是虚言……”
“别真是狐狸托生的吧……”
“谁不说呢,普通人哪会打洞啊……”
“会打洞的,也不一定都是狐狸……”
“容貌倒是更有几分……”
身后那些话语逐渐有了些轻佻的意味,贺兰破脸色愈难看,侧过脸冷声道:“诸位若是无事,右转藏室有的是东西拿给你们品头论足。”
场中一众噤若寒蝉。未几,在疏桐的示意下,宾客由小厮丫鬟们领着渐渐散开,或进了屋,或去了棋室、画室和马场,还有一部分留在院子里的,也离得远远的,并不敢侧目。
贺兰破大步流星上了花圃,拉了祝神就要走,却听祝神见短暂的闷哼,反将他拽住,不肯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