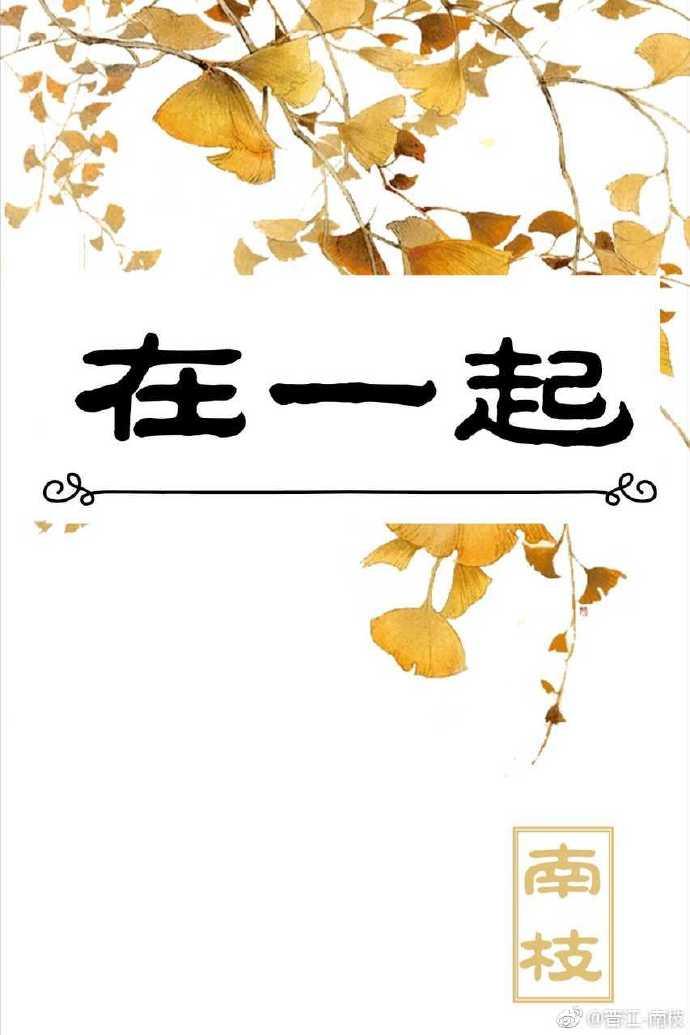UPU小说网>积点德是不是骂人的意思 > 第187頁(第1页)
第187頁(第1页)
還有……
宇文顥怎麼看怎麼覺得男人渾身上下都充滿了「你就說我帥不帥吧」的嘚瑟樣。
「嘿。」
「嘿。」
兩人笑著打招呼,並沒有更多的言語,只是專注地望著彼此。
一旁的牧民同男人說了句什麼,便策馬跑開了,廣袤的天地間,仿佛只剩下了馬上馬下的兩個人。
男人曾經象牙色的臉如今是健康的小麥色,他依然笑著,望著站在馬前仰頭凝望自己的宇文顥,藍色的帽衫和牛仔褲,襯得男孩更加的挺拔勻稱,貌似也健壯了不少,不再似從前那般瘦弱蒼白,因著趕了幾天的路,身上的衣衫皺巴巴汗津津的,清俊的面容也被草原上的風吹得兩頰微紅。
男人伸出粗壯的手臂,邀請男孩上馬。
宇文顥遲疑了一下,他還從來沒有與人同乘過一匹馬。
「歡迎來到我的牧場,白又亮同學。」
鮑皇叔的聲音在草色繽紛里格外的性感誘人。
宇文顥緊緊了身上的背包,伸出手臂,兩手相握,都帶著熱暖的汗意,男人的手掌滿是粗硬的厚繭,在揮鞭放牧的日子裡,早已褪去了往日的細皮嫩肉。
緊緊握住,用力一提,宇文顥顛成八瓣的屁股又重重地落在馬鞍上,也穩穩地落在了男人的懷抱中,還是那抹若有無若的古龍水,混雜著男人身上汗水的味道,微盪在男孩的心底。
男人的手臂攏了攏宇文顥精瘦的腰肢,戲謔道:「嘖,胖了。」
「呸,見面就不能說點好聽的?」
「更有勁了。」
「呸,要你管。」
「文濤給我打電話,我合計著你昨天就應該到了。」
「在市里住了一天,給乾媽買了點東西,早上車子又壞了。」
「學校放假了?」
「嗯,十幾天吧。」
「誒我說你這學上個沒完了?一個畫畫的拿這麼高學歷幹嘛?就算官司打贏了,再有錢也不能這麼不務正業吧?」
「博士生怎麼就不務正業了?我又不是學渣,能上幹嘛不上?」
「誒你這就不太友好了,學渣怎麼了?還不是照樣睡了你這個學霸。」
「媽的缺德,咱倆現在是純潔的友誼,還請注意您的說話方式。」
「哦,是嗎……」
駕——
男人輕輕一磕馬肚,駿馬揚開四蹄,向不遠處冒著炊煙的氈房噠噠地跑去。
「媽媽,我們餓了,開飯嘍。」
宇文顥這幾天裡,也住過兩次牧民的氈房,但是古蘭丹姆的氈房尤為乾淨、漂亮,掛毯、花氈,裝飾得五顏六色卻又花而不亂,斑斕而又明快,而且……屋裡為毛這麼多人啊,怎麼又是滿滿地一大桌子啊,所有人團團圍坐,和這氈房一樣,全都是五顏六色的。
宇文顥先是被古蘭丹姆親吻擁抱,好像又胖了點,宇文顥的兩隻手臂快要摟不過來了,喊著乾媽,細細端詳了下,古蘭丹姆堆滿笑容的皺紋里,依舊風情不減。
然後屋裡每一個人又輪流把他抱了一遍,這個阿依叔那個古麗嬸的,宇文顥笑到嘴角輕抽,真是個熱情的民族啊!
又吃到古蘭丹姆的手把羊肉和烤饢了,宇文顥餓壞了,敞開肚皮吃,他吃得歡,古蘭丹姆笑的就越歡,三個女兒中只有小丹跟著媽媽回了疆,為了歡迎宇文顥,還特意獻上了疆舞,漸漸地,很多人都加了進來,鮑皇叔的牛逼永遠都是吹不完的,輕聲對宇文顥說:「都沒我跳的好,看我的。」
男人下了場,隨著舞曲又抖起肩膀晃起頭來,宇文顥的笑微微凝在唇角,恍恍惚惚的,時光仿佛又穿越回到那年的多倫多,在庫伯太太家的花園裡,鮑皇叔舉著酒瓶也是這樣跳著唱著,回眸的一瞬間,鎖定了隔壁窗戶里的宇文顥,他們隔空相望,看的宇文顥心裡一慌,此時此刻,心跳的依然劇烈,只是卻多了一抹往昔如流水的淡淡感傷。
蓮華牧場的迎賓筵席,一直持續到夜空如墨,星光璀璨,人們點起了篝火,喝著奶茶,吃著烤羊腿,談論著各自的喜怒哀樂。
彎曲的河水如銀絲帶般緩緩流動在草原上,發出粼粼的波光,抬頭仰望,宇文顥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星空,撒滿了鑽石。悄悄遠離一方的歡鬧,坐在浸著夜露的斜斜的草坡上,宇文顥的心依然無法回歸往日裡的平靜。
夜風吹過,不禁打了個寒噤,身上瞬間一暖,跟過來的鮑皇叔將一件棉襖披在了他的身上,順勢也在一旁坐了下來。
「即便是夏天,這裡的夜晚也涼,別感冒了,我的客人。」
嗤,宇文顥輕笑,又接過他遞來的熱奶茶,微微抿了一口,還是皺了下眉頭,依然不太習慣這個怪怪的味道。
鮑皇叔的襯衫外套了個皮馬甲,更像美國西部片裡的牛仔了,一隻手拎著啤酒,隨著不遠處的鼓曲,輕輕敲打著馬靴,不時地吹著口哨,一派逍遙自在。
「你現在……生活的很好。」宇文顥由衷地說。
鮑皇叔乜著眼瞅過來:「你現在……不也挺好的嗎?」
宇文顥躊躇不語,繼而淡淡地說:「談不上多好,也無所謂不好,只能說是湊合,學習也挺累人的。」
鮑皇叔沉吟片刻,又問:「你媽媽還好嗎?聽說她又跟你爸爸回國了?」
「嗯,官司打贏後,他們就回去了,我媽說,我爸又買了套房子,跟馬女士他們分開過了,錢呢,損失了不少,但也夠他們養老的,我現在自由了,可以隨時回國去看他們,他們也可以來多倫多看我,夏天過來住上一段日子,我帶著他們四處玩玩,秋天一過他們就回去,嫌多倫多太冷,其實,這麼多年了,他們不太習慣我的生活,我也不習慣跟他們一起生活,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還是分開過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