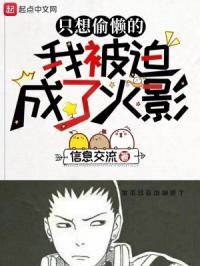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异世夫君来种田免费阅读完整版 > 第56章 徐巧1(第2页)
第56章 徐巧1(第2页)
赵锦润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与程大哥所说的一样!赵锦润好整以暇地反问:“徐大人以为是什么?”
胯下的马匹打了个响鼻,无聊地踏了两步,赵锦润拍了拍马头,示意它安静点。
铸造私银、勾结山匪,这些都足以削了徐巧的官帽,但铸造私银一事牵连甚广,背后之人程锋虽然没有点明,但赵锦润也能猜到一二,还有对于程锋效忠的人,赵锦润也有点头绪。剿匪的这几天里,赵锦润迟钝地明白自己上了程锋的“贼船”。但为了庆远侯府,赵锦润也没有别的选择,说来说去,这事儿也是因为他擅自跑来霁州才惹上的。
既然铸造私银一事不能摊到明面上,勾结山匪的证据还没有掌握,就不能定徐巧的罪了吗?
他悠然的姿态加深了徐巧的疑虑,徐巧也在想,赵锦润是要拿什么给他定罪?是他纵容部下敛财被现了?还是通判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强夺良家少女被知道了?又或者是家奴仗势欺人、打死粮店老板的事?还是说底下那些县丞故意加重税收被查出来了?
心思在这些属下里转过一圈,徐巧又觉得问题不大,不论是哪一件,他都能撇清关系,能在霁州只手遮天三年,他徐巧可不是什么草包废物。
“徐大人是在想什么?”赵锦润故意叹了口气,“那么多坏事,您可想到是哪一件了?”
“赵大人莫要在这里信口雌黄!分明是赵大人借着钦差之名、行恶徒之事,纵容那二人在我府上为非作歹,还害我母亲、害我妻儿!”
“你妻儿不还站得好好的?”赵锦润眼底是浓浓的嫌恶,“徐大人给活人定上死罪,是有什么谋算不成?”
“我徐巧自认为行得正坐得端,不知赵大人要把什么罪名安在我头上?赵大人可知,谋害朝廷命官也是大罪!”
徐巧看向旁若无人地小声说话的程锋和宋羊,这两人也很轻松,没有给他一个多余的眼神,在他们旁边的是徐菱,他不是第一次推这个女儿去帮他做交易了,徐菱向来很听话,但这一次,徐巧总觉得她哪里变了。把徐菱看作背叛者,徐巧想着回头再跟她算账,收回视线时,扫过徐进惊惶的脸,徐巧多看了一眼,才认出这是他儿子。他似乎很久没跟儿子说过话了,不过他与这个儿子也不亲近就是了。还有一些苟延残喘的徐家下人惊疑不定地看着他,而他脚边,徐夫人也吓坏了,呜呜地哭个不停。
“哭什么!闭嘴!”徐巧呵斥。
徐夫人脖子一缩,眼泪还不住地流淌,却不敢出一点儿声音。
“赵大人直说吧,徐某洗耳恭听。”徐巧向心腹部下使了个眼色,心腹点点头,徐巧便知道,求助的消息已经顺利送出去了。
“那好,”赵锦润也跟程锋交换了眼色,程锋点头,赵锦润这才朗声道:“二十年前,凶犯徐巧蓄意谋杀三河里柳乡绅的千金柳如系、三河里徐家村秀才徐广迎、以及自家胞弟徐秦!人证物证具在!来人呐——给本大人拿下这十恶不赦的混账!”
赵津手向前一挥,数十人冲上前,徐巧的人立即提刀抵抗,赵锦润笑起来:“徐大人这是要拒捕?根据本朝律令,拒捕逞凶者,罪加一等!”
“赵大人口口声声说徐某杀了人,可有证据!”徐巧被那几个许久不曾听过的名字乱了心神,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二十年过去了,那件事还能有什么证据不成?他看向程锋和宋羊,意有所指道:“赵大人可不要被小人哄骗了!”
本想安安静静看戏的宋羊实在忍不住:“这个时候就不要挑拨离间了!徐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了那么多坏事,已经走到头了。”
程锋适时地下令:“带上来。”
一直隐藏在暗处的卓夏走出来,身后的属下领着两名老妇。
其中一个,正是徐巧的生母徐陈氏,另一位身形憔悴、衣衫褴褛,看起来只是个叫花子。
徐巧不认识那叫花子,目光只在母亲身上多有停留,眼底波澜四起,最终又归于平静。
徐夫人却认识那个叫花子,这人来闹过好几次,常常挑老爷不在府的时候,说她家老爷杀了自家小姐,要讨一个公道,徐夫人不耐烦应付,次次都将人打了。
那天,宋羊给徐夫人送点心,临走时听到杨嬷嬷跟徐夫人说谁又来闹了,宋羊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叫玉珠去打听了一下,而后便让卓夏去破庙找到这名老妇。
“徐巧,你可认得这人?”
“不认识。”
“你个黑心肝的!你不认得我,我却忘不了你!你化成灰!我也能把你认出来!”老叫花子对着赵锦润磕了几个响头,“青天大老爷啊!这人杀了我家小姐!还请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啊!我家小姐……死不瞑目啊!”
赵锦润之前就得了消息,闻言道:“只管说出你的冤屈。”
“草民是岭南澳州三河里,乡绅柳家的家生奴才,从小看着我家小姐长大,二十年前,我家小姐与徐家村的徐秀才两情相悦,只是老爷不同意,于是小姐决意与徐秀才……私奔。”说起这段往事,叫花子还斟酌用词,希望顾全自家小姐的名声,可见对柳小姐的忠心耿耿,“两人逃走不易,小姐的贴身双伺——秦哥儿,在探亲回来后,说他有个在念书的兄长,与徐秀才也是认识的,可以助小姐和徐秀才比翼双(飞)。”
“那一天,五月十八,我跟着小姐、徐秀才上了马车,同行的还有秦哥儿,还没出城,我现水袋漏了,便让小姐他们先走,自己去买水,结果被府上的家丁现,不得已躲藏起来,而等我赶上时,就看见——”